【SLAM!】潘天舒学术自述:一名老青年的人类学之旅
Solidarity 团结, Leadership 领导力, Action 行动, Motivation 自我驱动=SLAM!
中国民族学学会微信平台以“SLAM!”为召集令,号召青年学人培植开放意识,担负先锋角色。鼓励跨界发声,号召创意创新。SLAM!栏目,携手多个公众号,陆续同步推出“青年人类学者自述”系列。
首先我得感谢人类学“少帅”剑波老师,让我有机会在青年人类学沙龙这样一个场合倚老卖老,分享自己人类学之旅的体会和心得。
我与人类学的最初缘分来自30年前在英国利兹大学为期一年的交流学习经历。当时我作为复旦英美文学专业大三学生,有幸获得人生第一次海外游学和猎奇的体验, 无意之中为自己播下了一颗人类学的种子。在异域经历的与“他者”互相凝视,使我发现“文化”比文学更丰富,语境(context)比文本(text)更有趣(不管是艾略特的《荒原》还是玄学派诗人的传世名作)。至今我仍难以忘怀约克郡的风土人情,尤其是那带有鲜明特征的口音和俗语。大四毕业留校后,我又去农村支教一年,在田野体验中更感受到做实地调查的乐趣,觉得“小城镇”的“大问题”实在太多(此时耳畔响起多年后沈原和郭于华老师用他们特有的腔调说出的“小城镇还真成了大问题啦”)。顺便说一句,89年过年回苏州过年与老外婆闲聊,说起当年她上小学时与费孝通同坐一条板凳的趣事。她还说“费孝通喜欢杨绛,不过杨绛喜欢伲钱家人”(必须指出,在人类学者眼里,老太太混淆了“家”作为Lineage和Clan概念的原则性区别)。我以为老外婆的八卦,未必是事实,直到10年后在北京听到沈原和郭于华说:这事谁不知道啊。后来小舅舅告诉我:外婆在读振华女中时与杨绛是同学,而且她们都是王季玉校长器重的理科和文科“学霸”(言下之意,外婆说的都是事实)。当然,不管是八卦还是“事实”,从曼大的克鲁格曼到哈佛的赫兹费尔德都会认为,是当代人类学不可或缺的核心内涵。(顺便八卦一句:如果费孝通写成的《江村经济》是一部像他老师FIRTH《我们,蒂克比亚人》一样生动的民族志作品,没准杨绛还是会青睐让民族志讲故事的老同学的吧)。
话说1992年初,我在接待访问复旦大学的明清文学研究权威韩南教授(时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时,无意中谈到了自己在支教时读到的《小城镇大问题》,并就费孝通的社区研究对于转型中国的价值和意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实际上是一次计划外的面试)。韩南自上世纪50年代在北京留学时就认识费老。他说对费孝通学术遗产的评判,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和制度环境。在韩南教授的鼓励下,我申请去哈佛大学读研,并于1993年底作为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获得者开始在东亚地区研究专业委员会(RSEA)进行硕士阶段的学习,并于1995年进入人类学系攻读博士。
我的人类学专业学习起步于硕导华如璧(Rubie Watson),完成于由博导华琛(James Watson)负责的博士论文委员会。指导老师包括凯博文和赫兹菲尔德教授。华如璧和华琛是哈佛人类学著名的学术伉俪,而华琛、凯博文和赫兹菲尔德可以说是哥儿们,共同指导着几十名来自不同文化和学科背景的博士生和博士后。我有幸从这一特殊的“家长制”和同学网络中得到教益和激励,顺利地完成了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在2002年后获得学位并找到教职。
从1998到1999年,我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Wenner-Gren人类学基金会和丰田基金会资助,在上海东南社区开展以历史记忆、“士绅化”和地方转型为核心议题的田野研究,析读1990年代结构性变革进程中发生在上海邻里各类人员身上的系列事件,以及他们面对世纪巨变的身份认同过程和和发展策略,最终写成题为Neighborhood Shanghai的哈佛人类学博士论文(经编辑后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从2002年到2005年我受聘于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外交学院和社会学系,讲授文化人类学、人类学理论、政治人类学、都市人类学、饮食与文化和“文化与政治”核心课程。经乔治城外交学院副院长贝蒂(Betty)推荐,我从2003年起在位于华盛顿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高级国际研究院(SAIS)国际发展部主讲发展人类学课程。这一经历为我日后写作《发展人类学概论》(2009年)打下了基础。
2005年我决定海归母校复旦大学,并获得导师华琛和凯博文的大力支持。华琛鼓励我在继续深化原来的上海城市社区历史记忆与社区发展研究的同时,更进一步聚焦于商业人类学、医学人类学、发展人类学三大核心来开辟复旦当代人类学的新天地。而我个人在研究实践中的角色也从独立研究者在不知不觉中转向项目协调人和主持人。2005年秋我在哈佛燕京学社访问期间,华琛安排我认识了英特尔“人与产品”(Peoples and Products)部门的研发人员。当时英特尔希望了解在中国农村这样的一个新兴市场(emerging market)中,信息交流技术(ICT)的普及情况。我在波士顿与他们电话沟通了2-3个小时,讲了我对中国农村的了解,以及博士论文的内容。2006 年我在回国的两周内,就在上海与英特尔研究员Susanne Thomas见面,开始了与英特尔的第一次商业人类学的跨界合作。当时我的搭档是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张乐天教授和上海大学的董国礼教授。张老师以《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一书成名,对中国农村生活有着极为深刻和独到的理解。我和张乐天老师各自的知识结构和生活体验可以说有一种天然的互补,所以后来我们把主要的田野地点定在了一个民工流出地城市和一个民工流入地城市。董国礼教授是阜阳本地人,对于土地流转和乡村基层治理见解独特。我们和Susanne Thomas一起设计了一整套方法操作指南,来对所有参与项目的人进行培训,这样也确保了项目中的每个人都能够按照人类学的基本原则去收集信息。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贡献是,我们讨论出了“影随”(shadowing)的具体方法。每个项目有不同的“shadowing”的方式。比如Thomas之前的工作经历是在手机厂商从事研究,她影随的重点在于记录人们拨出和接电话的瞬间,那个瞬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动作,表情,事件等。她很关注被观察者从做一件事情到做另一件事情的那个切换过程。而我本人1998年上海东南某社区做田野研究时曾经做过居委会主任的临时助手,工作内容就是跟着她工作一天,从访问孤老和贫困户到参加各种会议,还帮她做各种杂事,但更重要的是我田野体验的组成部分。这两种源自不同语境田野操作方法和技巧结合起来,就形成了我们在英特尔项目中对农户的“shadowing ” 的工作方法。研究人员对农户采用影随的方法,从家里到田间地头,到乡村社区,到镇上买东西,都跟着。在这个过程中Susanne认为,在完成一件事情,到下一件事情时,需要特别关注:比如从田里回来,遇到熟人,聊了多久。或者路上又去买农资啊什么的。同时我也意识到需要让一个男学生和一个女学生,分别跟随家里的男主人和女主人,这样能够得到互补和齐整的田野视角。这也是受到我的硕导华如璧和博导华琛当年在香港新界研究的影响 (夫妻二人当时在男女界限分明的村庄按性别分工进行田野研究)。在这个基础上,研究员在影随的基础上进行深度访谈。此时他们已经对乡村生活细节有了很多了解,再继续设计访谈问题,这样就很有针对性。从城市到农村。英特尔项目进入下一阶段时,我们和两位工业设计师(Industrial Designer)一起去阜阳和吴江(与海宁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相当的田野点),他们没有受过系统人类学专业训练,却很注重从当事人的立场和视角来看待问题,注意倾听当事人的声音,此时我和同事们都意识到了商业人类学广阔的应用前景。我们在2006到2008年间与英特尔和微软(中国)的合作项目,也给复旦人类学的应用性研究发展之路确立了较高的起点。
2007年秋,在张乐天老师倡议下,我与凯博文老师共同创建哈佛-复旦医学人类学合作研究中心并担任中方主任。中心自成立以来,一直注重跨学科交流的研究视角和手段,为学术探索和决策咨询服务。凯博文是研究中心的美方主任。作为当代医学人类学的领军人物,凯博文启发和引领无数医生、公共卫生专家、精神医师和社会科学学者,将医学人类学的观念应用于全球性的疾病预防和治疗,对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卫生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坚实的学理基础和实证依据。近年来我和同事朱剑峰与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徐一峰主任和哈佛亚洲中心的陈宏图教授(凯博文的学术助手)建立了持久的合作关系,先后进行了由上海市卫生局副局长肖泽萍教授牵头进行的上海市4-18岁儿童和青少年精神问题研究(田野调查部分)、由哈佛大学古德教授主导的应对精神疾病污名化策略以及哈佛大学凯博文教授主导的老龄化护理实践项目。目前我们中心正通过哈佛亚洲中心与江苏产业研究院合作开展一项老年科技与社会经济价值观的跨学科合作项目。从2012年起我和同事朱剑峰老师以圣路易华盛顿大学医学预科生为主要授课对象,开设以医学人文和全球健康为核心内容的国际课程。今年秋天,我和朱老师又和复旦社政学院的同事们合作,参与复旦基础医学院临床8年制学生医学人文导论课程的教学工作。
从2014年开始,我所在的教研团队成员与上海睿丛文化合作,在田子坊一起成立了复旦应用人类学教研基地,通过课堂教学、定期举行的跨界工作坊以及以医学和商业人类学为主要议题的项目合作,都大大拓展了复旦人类学的学科范围,并赋予其公共性、植根性和前瞻性的特征。十年前我听到有句话叫做“自由而无用”,常被用来概括复旦的大学精神。这虽然也是复旦当代人类学特色的某种体现,但我认为我们的学科发展更应该朝着“自由,有用,而且有趣”的方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实现费孝通“迈向人民的人类学”夙愿,走出坚实的第一步。
【论文】潘天舒 洪浩瀚|上海“麦工”意义世界的 人类学解读 基于田野体验的视角与洞见
刊于《社会》2011年第5期
摘 要 :本文以 2008 - 2010年在上海市静安区和黄浦区的麦当劳门店所进行的田野研究为基础, 通过检视其员工在日常工作环境中所采取的一系列调适性策略 ,探讨“麦工”( McJobs) 在全球化和地方转型特殊语境中的多重含义 。本研究初步发现 , 上海“麦工”的意义世界不仅仅是实在的文化生态景观 和精英话语制造出的符号 ,而且还受到跨国主义和地方转型这两股结构性力 量的主导和型塑; 本文在考察和分析普通“麦工”的地域文化认同 、价值观念 和工作策略的同时 ,强调社会分层和日趋多元化的城市生活方式对“麦工”体验过程的关键作用。
【推荐】雷蒙德·弗思|《我们,蒂蔻皮亚人》
《我们,蒂蔻皮亚人》
Firth,Raymond. 1936. We, the Tikopia.Boston: Beacon Press.
此书是雷蒙德·弗思(Raymond Firth)的代表作。虽然在上世纪40年代,他的学生费孝通翻译过导论格式的《人文类型》(Human Types)。但从实际影响力来说,《我们,蒂蔻皮亚人》无疑是弗思更具原创性、植根性和前瞻性的一部民族志作品。
1914年著名人类学者李佛斯(Rivers)出版了《美拉尼西亚社会史》(Historyof Melanesian Society)一书,其中有关蒂寇皮亚的材料来自传教士杜拉德(Durrad)的记述。而《我们,蒂寇皮亚人》一书的第一手材料,极大地弥补了这一缺憾。
弗思是最早将马林诺斯基的“参与式观察法”真正付诸田野实践并获得成效的门徒之一。马氏在序言中对他的褒奖之词包括“人类学研究的榜样”(1936:xxi)并将弗思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与贝森(Bateson)、本妮迪克特(Benedict)和米德(Mead)的已有成果相提并论。
此书对于21世纪的读者,至少有以下6大看点:
1. 如何从田野细节出发来建构理论模式(或者说如何不让理论预设来碍自己对人类日常行为的全面观察和揣摩),弗思的这本《我们,蒂寇皮亚人》提供了绝佳范例。
2. 针对结构--功能主义流派解释社会变化时所凸显的软弱无力问题,弗思强调将社会结构与社会组织(如亲族)加以区分的必要性,使田野工作者得以识别什么是恒定的模式(结构),什么是体现活力的个体和集体的真实行为(组织),好似行动理论出炉的先声。
3. 在本书第一版序言中,弗思提及《红楼梦》中“有血有肉”的亲属称谓对他的深刻影响(1936:xvi),丝毫不亚于摩根的《易洛魁联盟》。
4. 他对于亲族的定义顾及了当地社会生活和组织制度的方方面面,从居住模式到饮食实践、物质文化、传统信仰等等路径,使得人类学者在研究家庭和婚姻实践时比社会学和性别研究领域的同行有着更加丰富的视角。
5. 田野技巧示范之作。以男性成人仪式(割礼)为例,弗思强调了观察者的理论解释以及当事人对于实际发生事件的说法之间的区别,展示了如何从细节描述中提炼出抽象特征的具体做法(1936:382)。
6. 如果我们用挑剔的眼光和后见之明来再度审读《我们,蒂寇皮亚人》的话,会发现一些硬伤。如:在论及蒂寇皮亚传统宗教实践时,弗思显然忽视了相当多的当地人已经成为基督教信徒这一重要信息。但教训本身也是一种财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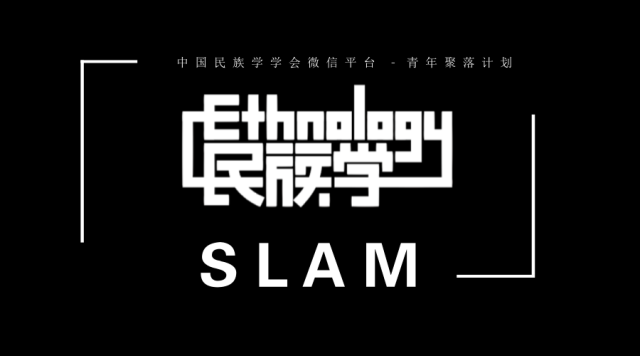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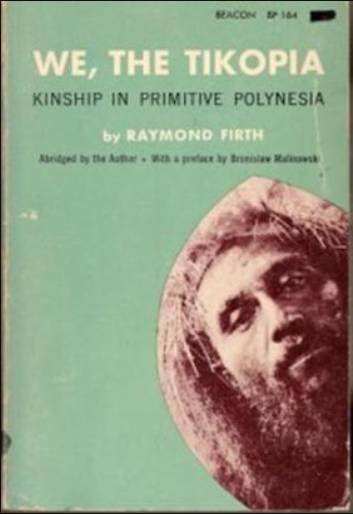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4520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4520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