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AM!】赖立里学术自述:与人类学相遇,是我今生最大的幸福
Solidarity 团结, Leadership 领导力, Action 行动, Motivation 自我驱动=SLAM!
中国民族学学会微信平台以“SLAM!”为召集令,号召青年学人培植开放意识,担负先锋角色。鼓励跨界发声,号召创意创新。SLAM!栏目,携手多个公众号,陆续同步推出“青年人类学者自述”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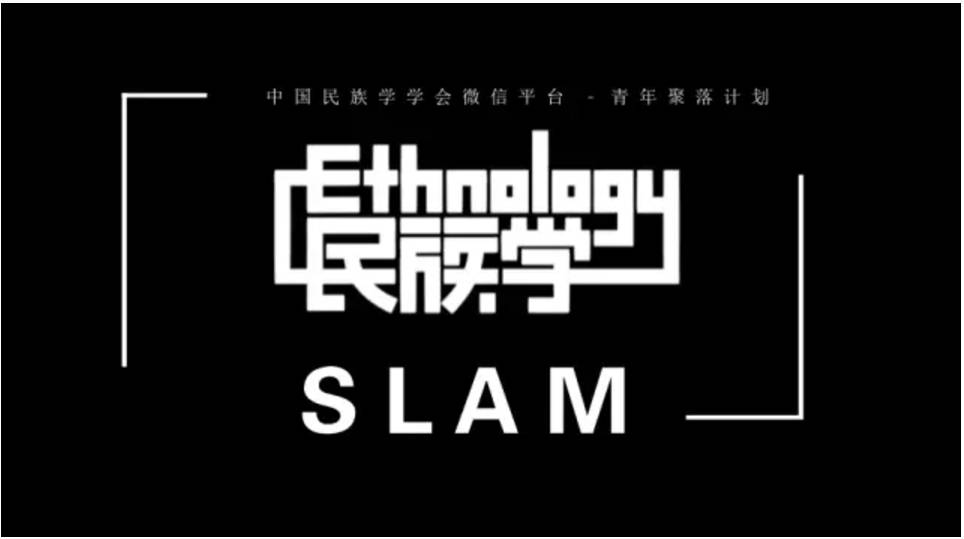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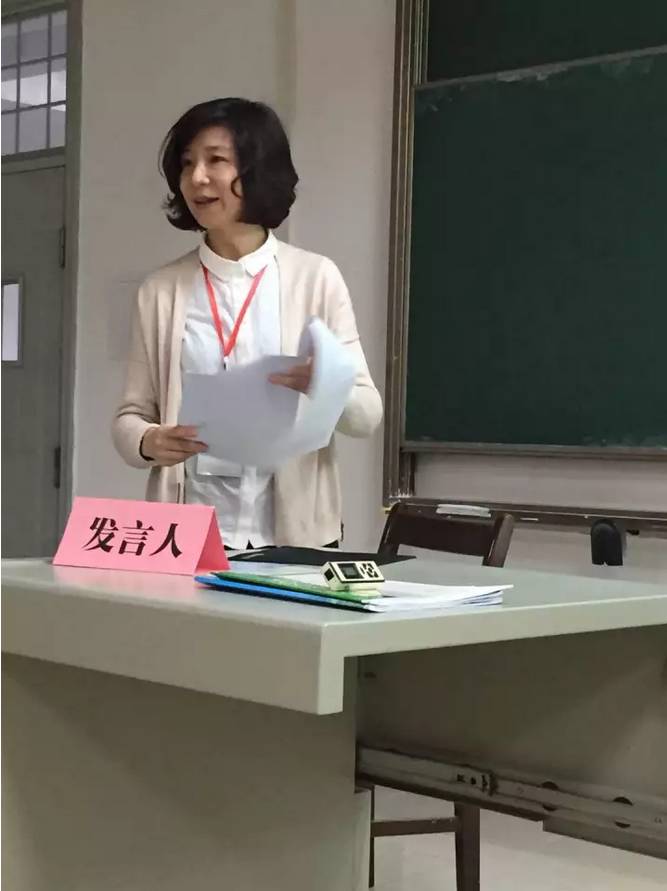 很多人都知道我的中医背景,这也是我“自然而然”地从事医学人类学的缘由。但其实我更愿意说我从事的是知识人类学(Anthropologyof Knowledge) 研究。
很多人都知道我的中医背景,这也是我“自然而然”地从事医学人类学的缘由。但其实我更愿意说我从事的是知识人类学(Anthropologyof Knowledge) 研究。
当年,我在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本科学习以及之后留校工作的经历带给我很多关于科学以及科学化问题的思考。于是我在UNC-ChapelHill的硕士论文将中医作为着眼点,在STS (Science & Technology Studies)的框架之下,考察了中医院校的“科学化”话语;具体来说,“科学”的身份和含义是我考察的关键。通过比较1930年代和2000年代的科学化尽管是以中医为研究对象,研究的目的则是观察一个历史深厚的本土知识与实践的现代遭遇,以及从中折射出的当代中国社会无所不在的“科学”如何从外来而逐渐在地化的历史过程。科学、尤其是科学主义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举足轻重的一个意识形态,科学人类学研究对于把握当代社会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我的跨学科背景形塑了我对物质性生活的人类学研究(anthropologyofmaterial life)的研究兴趣。具体来说,这样的研究将身体、实践,以及日常生活都作为一种唯物主义研究的客观对象,同时将它们置于深刻的历史与文化场域中进行分析。在我的博士论文田野调查中,我坚持认为村民的身体本身即具备鲜活的主体性:衣、食、住、行、谈话、劳作、回忆过去、筹划未来,这些活动都可以看作唯物的实践活动来加以分析。正是在这样的方法论指导之下,我的博士论文从空间、身体、日常生活及社会实践等方面,探究了建国以来制度化的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对普通村民的生活产生的深远影响。这一研究基本还是在经典的文化人类学框架之下进行,着力考察村民的日常卫生、社会交往、历史记忆及文化等方面。经过这个博士论文研究的人类学成人礼,我正式将我的学术规划定位于文化人类学之下的知识人类学研究。
回溯毕业之后的所谓学术经历,我主要做了这样两个研究:
1、关于民族医药的人类学研究。
这是我与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冯珠娣(JudithB.Farquhar) 教授的一个合作研究项目,此项目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承担的科技部重大课题“抢救性挖掘、整理少数民族传统医药”为背景进行。主要致力于理解傈僳、阿昌、壮、瑶、土家、羌、黎族等7个民族的传统知识与实践。在当下国家主导的重建少数民族医药知识体系的高瞻远瞩战略中,以及围绕着传统医药知识产权的全球政治中,这些既古老又新生的民族医药如何确立自己的知识体系并获得传承。本研究项目以知识体系而不是某一群人或者某一特定社会作为研究对象,这对于人类学研究来说还是一个相对较新的领域。
我们提出的具体问题主要包括:如何理解知识生产过程所包含的异质多样的实践,这些实践如何帮助我们了解传统知识建构为现代知识体系的过程?对传统知识的规范化使得国家甚至全球的医疗传承成为可能,如何理解知识的规范化对这些长期以来都处于分散和“经验性”的状态的传统知识起到的效应?这些问题都围绕着传统知识的现代处境及其生机,在当代中国具有相当深刻的现实意义。
同时我自己的关注点也包括依然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行政体系在当下特定的社会、历史、政治情境中如何治理知识(governmentalityofknowledge)。
2、关于高新技术的人类学研究。
我自2013年即开始了一项关于辅助生殖技术的社会影响的人类学研究。这一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呈现关于生殖技术的交错、并置的多重视角,以及这些视角如何描述和解释与这一高新技术相关联的实践及其相应伦理问题。关注的重点是接受辅助生殖技术的夫妇们对这一技术的期待、认识、经历,和评判。
辅助生殖技术的外行知识与专业知识在不孕不育人群中的博弈与实践,这也是我的知识人类学研究的系列之一,同样涉及到处于边缘的非主流传统知识与民间知识(folkknowledge) 在现代社会的处境、及其历史与未来。同时,这一研究还关注到辅助生殖技术对“亲属关系”、“社会性别”、“老龄化”、“婚姻体系的变迁”、“家庭形成”等社会科学领域基本认识所产生的极大挑战和深刻影响,也属于知识体系人类学研究范畴。
人类学让我从深陷于中的“中医是否科学”的迷茫中走了出来,我对人类学以及科学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STS)有着非常强烈的认同感。很庆幸自己找到了愿意从事一生的事业。与人类学相遇,是我今生最大的幸福。
【论文】赖立里、冯珠娣|知识与灵验: 关于民族医药发展中的现代理性与卡里斯马的探讨
刊于《思想战线》2014年02期
[内容提要]
在国家主导的“发掘整理少数民族医药”的宏大项目中,针对民族医药开展的知识生产和体制化建设是其中的核心内容。随着体制化进程的展开,医药知识的变革似乎失去了其本来的魅力:民族医药所内涵的地方习俗、身体,乃至医生个体的卡里斯马 (Charisma) /灵验性都面临消失的危险。然而新的理性化的知识体系也可能产生更多更广泛的治疗形式,更易传承,并出现新型的卡里斯马/灵验性。这也许是许多人都愿意参与的博弈。
【推荐】余成普|地方生物学:概念缘起与理论意涵 ——国外医学人类学新近发展述评
推荐按语:
余成普博士的这篇文章细致梳理了医学人类学家罗克提出的“地方生物学”概念,更是明确提出生物医学(即西医)本身就是“民族医学”,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并非“不受文化限制”(culture-free)的科学系统,而是植根于特定的文化前提和认识论基础,镶嵌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之中。这样对称性地对待生物医学与其他医学,对于把握当下活跃的各种医疗实践至关重要。同时,“地方生物学”概念挑战了生物-文化的二元关系,强调对身体的认识并非普世唯一(即生物医学之解剖学意义的身体),“地方身体”的概念呼之欲出,这也呼应了我们在“知识与灵验”文章中强调的民族医药所内涵的地方习俗、地方身体,乃至医生的卡里斯马(灵验性)与医疗实践之难舍难分的关系。
刊于《民族研究》2016年第6期
摘要:医学人类学家罗克(Margaret Lock )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地方生物学(local biologies)概念,强调文化和生物过程长期交织而导致的生物社会差异,以反对生物医学普适性身体的假定。本文尝试通过对地方生物学这一概念及相关论著的梳理,展现出医学人类学新近发展中三个相互关联的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的论争和理论主张:第一,反对身体的标准化,主张生物和文化过程的地方变异和可塑性;第二,反对生物-文化、先天-后天的二元对立,在具身化(embodiment)的策略下强调生物文化的整体性和辩证关系;第三,反对基因决定论,借助表观遗传学(epigenetics),探索生物-文化连接的微观机制。
(请感兴趣的读者自行查阅文章原文)
青年人类学者学术自述计划由人类学公众号联盟联袂推出。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4520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4520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