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AM!】龚浩群学术自述:在相遇中成为自己——我的海外民族志研究经历
Solidarity 团结, Leadership 领导力, Action 行动, Motivation 自我驱动=SLAM!
中国民族学学会微信平台以“SLAM!”为召集令,号召青年学人培植开放意识,担负先锋角色。鼓励跨界发声,号召创意创新。SLAM!栏目,携手多个公众号,陆续同步推出“青年人类学者自述”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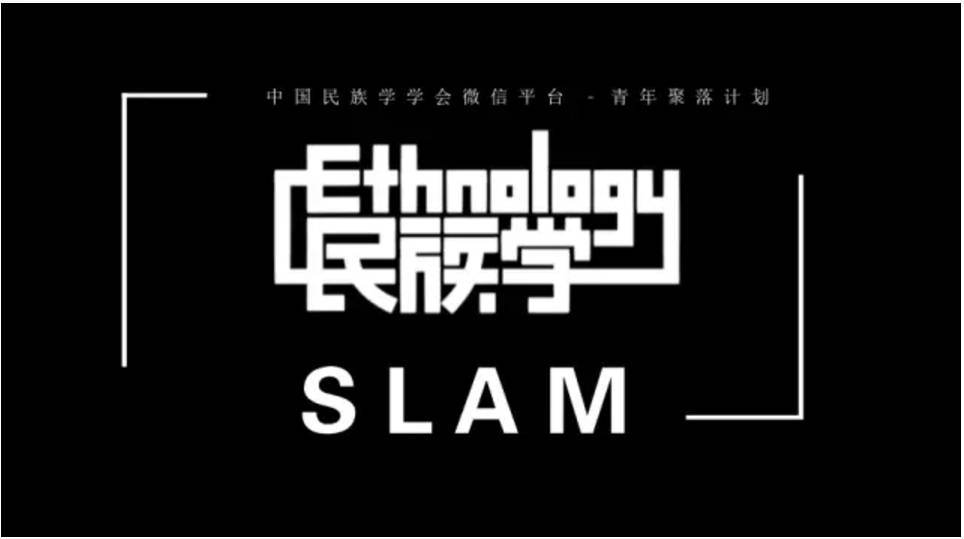

到目前为止,我的人类学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关于泰国社会的宗教人类学研究。从2003年到泰国开展博士论文的田野调查开始,我的研究最关注的是宗教与政治的关系。我最初是在泰国中部的一个农业社区开展调查,关注到佛教与现代泰国的公民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阶段我最大的收获是感受到佛教徒、臣民和公民的身份如何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我也试图在经验观察的基础上思考现代民族国家的公共性逻辑的问题,亦即如何在利用传统文化网络来建构现代社会的公共生活。当时我认为泰国的经验为中国提供了参考,在中国我们面对太多的裂痕与创伤,而泰国的历史却是在连续性中前行——我似乎在泰国发现了乌托邦。在我的博士论文答辩时,几位委员都提出关于泰国社会中的冲突的疑问。在当时的我看来,泰国社会固然存在公共性逻辑的内在矛盾,但是,这种矛盾的表现形式仍是模糊的。
2006年在泰国发生的军事政变改变了泰国的政治前景,政治冲突至今仍未平息。农村民众与中上阶层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了白热化的程度,颜色政治与街头暴力似乎成了泰国政局的代名词。在这种情形之中,我开始思考当代泰国的激进社会运动,包括佛教改革运动。如果说始于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佛教改革运动为泰国中产阶层和知识精英倡导的民主改革提供了价值依据,那么,如今的中产阶层如何看待佛教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呢?佛教改革运动与当前中产阶层的政治主张之间有何关联呢?从2013年到2015年,我两次在曼谷开展关于中产阶层佛教实践的田野调查。我观察到身体技术成为了中产阶层禅修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修行者借助身体技术来锤炼内心应对世事变幻的能力。与此同时,修行者也将现实问题的解决之道寄托于个体化的宗教实践,否认了生命之苦的社会根源。个体化的修行方式既造就了修行者的精神自由,同时也反映了他们的政治困境。有意思的是,这两年南传佛教的修行培训班在中国内地也开始流行起来,并受到一些城市白领的青睐。开展中、泰城市中产阶层修行实践的比较研究,或许会对亚洲社会的宗教个体化问题产生有趣的思考。
在我的研究经历中有一个小插曲,也构成了我研究中的第二个部分,即对于美国地方社会的宗教与政治的调查研究。我于2010-2011年在哈佛大学访学期间在波士顿水镇从事了一年的田野调查,当时主要是想了解美国地方社会的公共生活状况。具有新英格兰特色的自由派宗教吸引了我,我感兴趣的主题包括教会政体及其现代转型。同时,我也对当地人的法律观念、社会正义项目与地方政治实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惭愧的是,我的关于美国社会民族志的写作计划因为自身的懈怠一直未能实现,不过,对于美国社会的考察促使我从之前的泰国研究中跳出来,让我在重新面对泰国社会时有了新的参照和更多批评性的思考。例如,作为参与观察者,我在泰国和美国强烈地体会到政治文化的差异。在泰国做调查时我时刻努力地通过身体语言和谦逊的姿态将自身编织到当地人的长幼秩序中,以此来获得身份认同感。而在美国,我必须通过独立的个性化的言说来获得存在感。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语境中,政治观念和日常实践也就具有了不同的内涵。
我的研究的第三个部分开始于近两年来关于海外中国人的研究设想和对海外民族志研究的方法论反思。我目前有两个研究计划:一是研究泰北清迈的中国游客与当地人之间的文化互动与文化冲突,2017年暑期我在清迈开展了预调查;二是研究汉语志愿者的国外工作经历对他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轨迹的影响。我的总的想法是想看到今天的中国与世界之间如何相互影响。在海外民族志研究的方法论反思方面,我希望从关于文化间性的讨论进展到对文化三角的认识,突破“我与他”的二元关系,更充分认识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存在的多种关系性力量,并尝试探讨“我们的人类学”的可能性。此外,我也借助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的平台,探讨海外民族志研究、知识共同体与区域社会共同体的形成途径,倡导中国学者与其他来自第三世界的学者之间互为知识主体。
这些年来,困扰我的一个问题是海外民族志研究对于中国知识界有何意义。我提出来供大家讨论的问题包括:如何认识海外社会文化研究中的中国意识?是应该先确立中国意识,再向外研究,还是在与他者的相遇中发现和反思中国意识?海外民族志应当如何呈现中国意识?
另外一个值得大家思考的问题是人类学与时代的关系。在所谓“大国崛起”的今天,中国人类学能做什么?在人类学研究中,如何通过具体的人物和事件来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如何理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动力和外力?
最后一个涉及教学实践的问题是,在人才培养方面我们如何推进海外民族志研究?在当前学科设置的背景下,中国人类学如何通过新的学术增长点来获得学科发展空间?人类学与区域研究应当形成怎样的互动关系?
回顾起来,当年从事海外民族志研究是为了寻找不同于中国社会的另一番天地,而今天,我更希望从多重关系当中来重新审视自我,这既包括中国与世界其他区域的关系,也包括海外研究与中国研究的关系,以及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或许我们不再是通过他者来绕道地理解自我,而是在“我与你”的相遇中成为我们自己。
【论文】龚浩群|身心锤炼:关于泰国城市中产阶层佛教修行实践的初步分析
刊于陈进国主编,《宗教人类学》(第七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内容摘要:
宗教的现代转型是当代世界面临的普遍问题,也是宗教人类学与宗教社会学的重要研究课题。关于当代泰国城市中产阶层佛教信仰与实践的研究可能为检验和丰富现有的宗教研究理论提供有益的个案。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泰国的现代社会转型催生出佛教改革运动,并对城市中产阶层的信仰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佛教改革运动强调个体作为道德行为主体的地位,因而强化了宗教实践的个体主义色彩;另一方面,佛教改革运动又产生出新的宗教组织形式、新的世界观和新的公共话语,试图回应当代社会在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本项研究初步发现,佛教改革运动对个体修行实践的强调发展出对于身、心、法的关系的深入体验和一系列的身体技术。个体通过多样化的修行路径选择,达到从不定、定到内观的不同层次的身心状态。个体修行者关于“感知身体在当下的存在”的表述,暗含着身体技术所造就的自我认同的时空维度,并可能成为个体与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出发点。
【推荐】李荣荣|从内在幽深处展望世界社会——读贝克《自己的上帝》
推荐按语:
李荣荣博士作为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自己的上帝——宗教的和平能力与潜在暴力》一书的中文译者,从宗教的个体化与公共性的角度对该书进行了深入的评述,探讨了宗教个人主义超越自我的可能性与有限性。贝克认为20世纪下半叶出现了个体化进程的民主化,而宗教的个体化体现为个人打破不同宗教之间的边界,创造出“自己的上帝”;宗教个体化可能会带来私人化,但也可能为信仰的新的公共角色铺平道路。贝克的论述主要基于当代欧洲福利国家背景下的个体化现象,那么,在当代亚洲国家,是否也出现了宗教个体化的趋势,个体的宗教实践和宗教的公共角色发生了哪些变化,如何从历史与社会进程的角度做出解释,而不把宗教个体化仅仅等同于个人的主观选择?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关注和开展比较研究的课题。
刊于《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4期。
结语:
《自己的上帝》提供了一个凝视当代宗教现象的新视角,为我们思考私人领域与公共价值的关联提供了灵感,并促动我们思考“自我建构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能够开启超越自我的可能性?”这一值得不断探索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讨论的宗教的个体化是基于欧洲宗教(基督教)的历史与当代表现、在欧洲现代性框架内提炼出来的概念。而欧洲的个体化路径并非普遍模型(Yan,2010;贝克,2011),其社会层面的前提是以文化民主、福利国家以及古典个人主义作为定义个体化进程的条件(Yan,2010)。同样,宗教个体化也是在相应背景下得以展开。就此而言,为了寻找宗教个人主义如何超越自我的答案,除了关注宗教或信仰本身之外,还须对社会、政治与文化等背景进行深入考察。
宗教本身既包含可见的制度性因素,也包含不可见的主观因素,因而,宗教研究中一个既重要又难对付的问题是在保持客观距离的同时又能理解信仰之主观维度。《自己的上帝》一书从信仰者的内在幽深处切入,剖析当代世界社会中宗教的个体化及其未预后果,指向世界社会的“世界”精神,为糅合宗教的主观维度与客观分析、微观洞察与宏观抱负提供了有益启示。
(请感兴趣的读者自行查阅文章原文)
青年人类学者学术自述计划由人类学公众号联盟联袂推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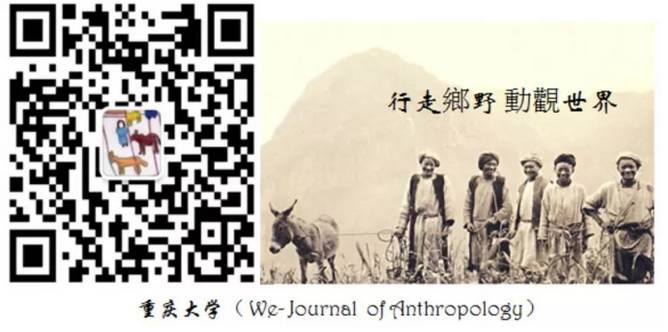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4520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4520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