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鸿保、林春】透物见人在江湖——基于武陵地区北部上古交通网络的一点思考
中国民族学学会
为您整合碎片化的学术讯息
(载陈井安、徐学书、喇明英主编:《民族走廊:互动、融合与发展》,成都:光明日报出版社,四川民族出版社,2015年。)
透物见人在江湖
——基于武陵地区北部上古交通网络的一点思考
胡鸿保,林春
(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长江水利委员会文物考古队 )
【提 要】借助考古发现透物见人,结合古文献和历史地理研究成果,展现武陵地区北部四个“亚区”间各自相对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错综复杂的交通网络,并借此探讨与民族走廊有关的问题。
【关键词】 考古学文化,族群,历史地理,民族走廊
武陵地区位于中国第二阶梯向第三阶梯的过渡地带,东界雪峰山、西止大娄山、南至苗岭、北达大巴山。境内层峦叠嶂、诸水滩险流急,前工业社会囿于技术原因开发难度极大,容易形成封闭状态。长期以来它一直是中华帝国的内在边陲。
本文所述的“武陵地区北部”,南起酉水和沅水下游;北至长江三峡;东抵清江口至澧水流域;西达乌江。该区还可再分为既各自独立发展、又有四条长江重要水系及无数陆路孔道相联结的四个亚区:长江三峡干流、乌江中下游、酉水和沅水下游、清江与澧水流域。
传世古文献关于武陵地区的记载不多,三代-秦时期及之前尤其如此。幸喜几十年来考古发现成果卓著,结合古文献、历史地理研究成果,让我们有缘透物见人,一探历史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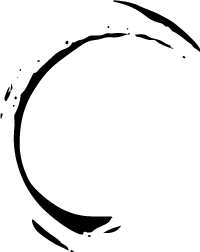
一、史前至先秦本区及周边文化概况
公元前6000~3000年,鄂西南、湘西北和渝东一线,在文化格局上,属于长江中游文化区彭头山·城背溪—大溪文化系统。湘西北澧阳平原以发达的农业和水利,成为长江中游文化区的中心;鄂西南、渝东区以石器制造、盐业输出等多种经营,参与长江中游文化圈的构建,是这一地区数千年的文化繁荣期。值得注意的是,六、七千年前大溪文化对外影响甚广,在粤南一带的同期文化中有浓烈的大溪文化因素,展示两个区域在此时就有顺畅的交流通道和频繁的文化联系[i]。
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屈家岭时代,由于全面技术革新引发的大范围社会转型,鄂西南、湘西北等地区衰败下来。活跃于渝中渝西、与长江黄河上游同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泛哨棚嘴文化,不断向本区拓展渗透,长江中游区文化中心逐渐转移至汉水中下游一带。
公元前2000年左右,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三星堆文化,从西往东强势推进横扫本区。原属长江中游文化区的鄂西南、渝东和湘西北部分地区被纳入长江上游文化区版图。本区文化面貌开始转变,逐步演成后世所谓的“巴蜀文化区”或“群蛮文化区”。
进入商时期,以陶器绳纹釜、灯形器、鼓腹罐为典型器物组合的成都十二桥文化、渝中西区(含乌江中下游)石地坝文化、渝东鄂西南(路家河文化)、陕南(宝山文化)四个考古学文化组成的文化联盟集团,遍布从成都平原至鄂西、陕南,乃至湘西、黔东北。
晚商至西周,这一文化联盟集团分崩离析,星星点点散播在上述各地。一支源于东南、炊具以方格纹鼎为突出特征、与越系族群有关的周梁玉桥类型文化进入鄂西、湘西北澧水上游,与路家河文化整合,形成新的考古学文化(清江流域仍以釜为主)。渝中渝西的同期文化承袭原先的文化传统,陶器以花边绳纹罐(釜)为主要特征,并将这一文化特质带进春秋战国时期甚至更晚。
西周中晚期,以高足鬲为特征的楚文化插入鄂西南,并渗入湘西北澧水流域,以定点、继而连线、而后成片的方式向纵深发展。楚文化可能最早定点于清江口一带,而后主要向两路推进:一路沿长江干流渐次向西,战国时期到达渝中;另一路春秋早期在澧水站稳脚跟后,逐渐扩张至今洞庭湖东岸、湘中、沅水下游及酉水乃至湖南全境。从物质文化窥测,楚系文化似无意彻底改造土著文化,交通干道一线楚文化因素浓烈,而在边缘地带,除了愈来愈占有优势的楚文化因素外,仍保存或浓或淡的其他族群的文化面貌。
公元前四世纪,秦制订灭楚战略线路:一路从武关南下攻取楚都郢;一路在并呑巴蜀地后水路东进,主要从乌江入酉水包抄楚之后方,终于在公元前277年夺下楚之黔中郡。然而,即便隶属于秦统治,本区在物质文化上仍主要呈现楚文化特性,在边缘地带巴、濮、越等族群文化特质顽强保留。秦统一后,本区战略地位下降,文化发展进入长时间停滞,区域内外族群间的合作、竞争及妥协史不绝书。[ii]
注释:
[i] 胡鸿保.深圳史前遗存所见之文化交流[J],南方文物,1992(3).
[ii] 此节综述参考林春《长江西陵峡远古文化初探》、《鄂西地区三代时期文化谱系分析》《鄂西渝东地区二里头文化遗存试析》等论文,载胡鸿保,林春. 文野互动[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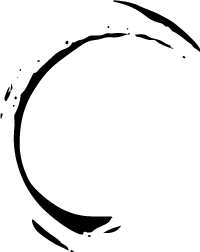
二、四亚区分述
前工业时代,水路航行是最经济、效率最高的交通方式,尤其在河网密布的长江流域,是先民的首选。先秦时期武陵山区北部可常年通航的有酉水及沅江下游、澧水、清江、乌江等。长江三峡干流、乌江中下游、酉水及沅水下游、清江及澧水流域这相互联结的四个亚区,由于地理位置、资源优势和政治军事原因造成的战略地位及变迁等因素,导致各交通功能的不同,并因不同而互补。
(一)长江三峡干流
武陵山区北部酉水及沅水下游、澧水、清江等东西向河流水路航运的兴盛和衰落,与长江三峡航运的开辟和发展存在因果关系,换言之,这些河流航道的繁荣,重要原因在于长江峡江航道的不畅。
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利用,以技术和能力(包括管理能力)为先决条件,人们只能从可掌控的事物出发,开发江河从小江小河开始,陆路水道,相辅相成。后世“千里江陵一日还”的场景,并非先秦历史真相。
三代-秦时期长江上中游之间的联胳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乌江转清江、酉水沅水一线,辅之以陆路[i]。三峡干流一线,发现大量三代时期遗存,三星堆文化东进浪潮过后,商时期的经济生活以渔猎为主,文化面貌主要是以绳纹陶釜为特征的巴系统土著文化。西周中晚期始,楚系文化从鄂西沿长江西进,同时把农业文明带进三峡,春秋时期楚文化成为三峡东部主导力量,但巴文化仍与之如影随形。成规模楚文化的最西地点在忠县一带,其西则是巴系文化的天下。三峡地区秦文化特征模糊,可确认遗存不多。
战国时期对长江航道的开发利用主要在长江支流上,《鄂君启节》中的主要航道在汉水和湘西、湘中诸水,长江干流航运的西部终点在夏首(江陵),即是明证。除了成集团行动的军事行动外,一般木船不可能全程通航长江干流、尤其在峡江一段。三峡航路开拓的主要推动力是巴楚秦间的战争。战争的需要促进了造船、航运技术和调度管理能力的创新和发展。
与湘西北先秦时古城林立的情景相比,从宜昌至重庆至今尚未发现先秦古城,不见酉水及沅水下游剑拔弩张军事对峙的态势,这表明先秦时期在三峡一线未发生大规模战事。
先秦时的三峡干流虽不能全程通航,却仍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它不仅提供长江沿线中短程航路,更是长江南北支流的水陆交通枢纽,如沿支流巫山大宁河登陆路往竹溪;从香溪通保康而后至汉水、抵达关中;沿乌江转湘西而华南,转清江而江陵,转沅水上游至安南,转西南抵云贵。这些航道与其间的陆路一同构筑起长江上游文化交流、人员流动的网络。
[i] 吴郁芳.先秦三峡航运质疑[J],江汉考古,1991(4);朱培麟. 三峡地区古代交通史略[J],重庆交通学院学报,2004(1).
(二)乌江中下游
乌江与酉水、沅水、清江及相互联结的陆路组成的武陵山北部交通网络,承担起长江上游与长江中游、华南、西南的联系。
乌江流域是数千年来长江上游南北走向文化沟通的大动脉,这条从今涪陵溯乌江往湘西、华南、西南地区的通道,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开通。
乌江口及其中下游一带发现最多、文化内涵最丰富的是三代时期文化遗存,标志该区文化的发展高峰。重要遗址有涪陵小田溪墓地、酉阳清源遗址、黔东北洪渡中锥堡遗址等。位于乌江口的涪陵小田溪战国秦贵族墓地是等级最高、出土有青铜礼器的墓地,今涪陵先秦时称“枳”,为巴先王陵墓所在地。这些遗存的文化面貌及所揭示的文化变迁,与重庆境长江沿岸同期文化基本一致,亦与成都平原、黄河上游同期文化发展趋势同步,“可将这一地区归属于‘巴蜀文化区’这一大的概念内”[i]。与武陵地区北部其他亚区不同的是,乌江中下游尚未发现楚文化遗存。
乌江航道又称“川黔道”、“牂牁、黔中道”,自然条件并不理想,近代之前,该航道最重要的货运功能,是把川渝长江沿岸出产的川盐运往不产盐的贵州、湘西和长江中游一带。这是这一条武陵山及周边居民的生命线,基于人类生存的刚性需求,成就乌江航道及由此向四周辐射的交通网络,持续数千年的不竭动力。在动荡分化的三代时期各政治集团军事行动中,该航道的交通资源成为争夺的目标,同时提升并优化乌江航道的品质和功能。
以数千年文化积累形成的交通网为背景,公元前3世纪武陵地区北部发生了著名的秦楚“黔中之战”。以往不少研究者以为秦军从巴蜀地出发,由今涪陵溯乌江转酉水东下伐楚。里耶城址和澧水、沅水下游一系列同期城址所反映的紧张军事态势,增强了此说的可信度。
秦统一后,武陵地区北部战略地位下降,乌江中下游汉以后文化遗存不再与重庆长江段同进退,而是出土大量印纹硬陶器。印纹硬陶器是华南越系族群的重要文化特质,这一现象反映了华南越人通过乌江北上。汉以后重庆长江段原“巴蜀文化”版块诸族群在物质文化陆续融入“汉文化”圈,而乌江流域仍是“群蛮”之地。由于对川盐的需求的持续性,川黔道依然是西南地区至长江、乃至北达关中地区的重要通道。
[i] 吴小华. 近年贵州高原新石器至商周时期文化遗存的发现与分区[J],四川文物,2011(1)。
(三)酉水和沅水下游
在自然地理上,先秦时期洞庭湖还未形成,澧、沅、资、湘水各自汇入长江[i],故彼时湘西的酉水和沅水下游,与澧水流域的交通和文化联系,当不如后世密切,里耶秦简中鲜有毗邻澧水的记录可作佐证。考古资料亦说明,酉水和沅水下游一线及以南,南方族群文化因素比澧水一线更为浓烈。
酉水是沅水最大的支流,主源发于湖北宣恩,沿湘鄂渝交界南流,经里耶、保靖、王村、到沅陵汇入沅水。酉水和沅水水量充沛、水流较平缓,是武陵地区最好的水路航道,为本区重要的交通线路。
数十年来酉水、沅水流域楚文化考古成绩斐然,酉水、沅水下游发现一系列战国城址:龙山里耶,保靖四方城,沅陵窑头古城,桃源采菱城(黄楚城),常德司马错城、张若城和索城(汉寿城)7座城。这些城的面积都不大,建筑时代主要集中在战国,当主要是秦楚巴之间战争的产物。
里耶遗址位于湖南龙山县南端里耶镇,是酉水上游的重要水陆码头,湘西北通往黔、渝的咽喉。里耶城址的年代分三期:第一期战国中晚期,系楚始建之迁陵县城址;第二期为秦代洞庭郡迁陵县县治;第三期为西汉。西汉初该城经历大规模修缮,城内布局有较大改变,暗示该城原有的军事功能发生改变。
里耶城址第一期遗存的主要文化因素为楚文化,同时出土有显著土著文化特征的绳纹陶釜等;第二期遗物仍然以楚文化因素为主,新出现折腹盆、陶量等秦文化器物;第三期遗物仍沿袭第一、二期时的楚文化特点。这种虽经秦统治、年代进入西汉后文化面貌仍保留楚文化主导的现象在湘西、长沙地区普遍存在。
除了楚、秦文化因素以外,可辨别还有其他族群文化遗存。
尤为瞩目的是,里耶城址1号井中出土了秦始皇二十五年至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22~208年)3万6千余枚竹简,简文为秦代迁陵县官署的部分档案。其中,里耶J116:52号简被称为“里程表”或“邮程表”,是秦代公文邮传、驿传专用的交通指南[ii]:
……鄢到销百八十四里。/ 销到江陵二百卌里。/ 江陵到孱陵百一十里。/ 孱陵到索二百九十五里。/ 索到临沅六十里。/ 临沅到迁陵九百一十里。/ □□千四百卌里。
该里程表呈现了两千多年前,从今汉水中游宜城沿秦楚大道(亦称“武关道”)至湘西沅水上游的水陆交通路线图。
有学者认为本简里程表的出发点是首都咸阳[iii]。本简中提到的秦代郡一级行政区有巴郡、洞庭、苍梧、南郡、内史五个。“内史”为秦朝首都咸阳地区的行政“特区”。据此亦可推断巴郡、洞庭、苍梧、南郡四郡的地理位置相近,且与咸阳有通达的交通联络。
里耶秦简提到的地名还有“酉阳”(洞庭郡属,今湖南沅陵)、“益阳”(今湖南益阳,资水流域)、“零陵”(今湖南永州)、“零阳”(今湖北兹利东)、“竟陵”(今湖北潜江东北,汉水流域)、“阳陵”(内史属县,关中地区)、轵(内史属县,关中地区)等。上述地名提供了一条从里耶沿酉水入沅水、入长江、再转汉水经丹水至咸阳的水陆并用干道。
除了有“巴”郡的记录外,里耶秦简未见秦代迁陵县往其正北、西、南方向的记载,但里耶遗址本身和周边的考古发现告诉我们更多的历史景象。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
1、古沅陵被誉“上通黔滇,下达江海”,与酉水航道的作用密不可分。里耶秦简中关于“益阳”(今湖南益阳,资水流域)、“零陵”(今湖南永州)的记录,表明里耶可通达资水流域和沅水上游,亦说明这是关中、巴蜀一带往华南的一条通道。
2、战国中晚期楚在湘西建立政权,一则是加强对南方的开发,更为紧迫的是防御来自上游秦和巴蜀的军事威胁,酉水和沅水下游一线分布着众多同时期具军事性质的古城,为武陵山区所仅见。严重的军事态势,使酉水里耶一线成为秦、楚对峙的前沿阵地和军事重镇。
3、酉水和沅水下游楚墓的规格比澧水一线偏低;江陵、澧水一带楚墓随葬品有一定数量的的青铜礼器,在酉水和沅水下游楚墓中则几乎不见。这些现象说明本区与楚国核心区存在很大差异,土著与楚人虽共存数百年,仍是貌合神离。有人认为,“沅水下游地区对于楚国而言,其历史战略地位远不如澧水下游、长沙等地重要”[iv]。
[i] 参见“先秦两汉时期洞庭湖水系图”[M]//邹逸麟主编.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103.
[ii]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物处. 湘西里耶秦代简牍选释[J],中国历史文物,2003(1).
[iii] 王焕林. 里耶秦简释地[J],社会科学战线,2004(3).
[iv] 湖南省常德市文物局等.沅水下游楚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811.
(四)清江与澧水流域
清江流域与澧水、油(繇)水流域地域毗邻,七、八千年以来就是资源互补型的亲缘文化体。在自然地理形态上,两个区域有很大差别:清江流域山高水深路陡、封闭而荒芜;澧水下游为河网切割的平原地貌,地形开阔,位于武关道往南延伸的陆路之要冲。两个区域在人文地理上也相差甚远,公元前6000~3000年澧水下游以发达的农业和水利工程成为长江中游文化核心区;而清江流域则是石器制造业、盐业等资源的补充地。两地之间有便捷的水陆路交通联系。沿长江可直达松滋;从清江支流渔洋关上岸,有陆路干道直抵澧水。
1, 清江流域
清江流域三面环山,由西往东在宜都注入长江,是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清江水流量大,坡降落差亦大,滩险湾多,并非理想的航道。流域境内主要有两条陆路干道,一条沿清江与长江之间平行伸展,从忠县南跨长江—利川—恩施—长阳—宜都北跨长江—江陵,今天的318国道、沪蓉高速公路和沪蓉高速铁路,在本区基本沿此古道运行;另一条从湘西—宣恩—建始—巴东—秭归—保康的西南往北偏东干道,今天的209国道在湘西北鄂西南段基本沿这一干道。两条主干道与其他干道或间道,与清江水道一起,构成一个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
从水路航运角度,清江一线,从古至近代,是三峡航运的重要补充。三峡航道每年数月的夏水封航期,却是清江航运旺季。因为清江航运须避航道之险滩。此时的货物由陆路转清江水道,再从清江口重入长江。
与其他三个亚区相比,古文献中关于清江先秦历史语焉不详;考古资料主要集中在清江下游长阳、宜都一带。
清江流域是武陵地区目前惟一出土商、西周青铜礼器的区域,且主要集中在清江入长江口处。15件青铜礼器中除一件的产地还不能确定外,其余14件均属“中原型”器物。
清江流域三代-秦时期考古文化序列总体上与长江西陵峡一带大同小异,但细究起来却不尽然,清江口与清江腹地、西陵峡一带,在某些时段,可能主要由于居住族群、还有遗址功能的不同,存在质的差异。
万福垴遗址是目前可确认的年代最早的楚文化遗存。出土的12件青铜器和共出的陶器,均为源于北方系统的鬲、尊、簋、豆等荆楚系族群器物组合,文化面貌单纯,或可视其为楚国官方进驻清江口的行为。与此现象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距此不远的长阳香炉石遗址西周时期遗存,出土物为巴系釜、圜底罐等,不见楚文化遗存。
北来文化直插清江口的现象,还出现在公元前2000年的宜都石板巷子遗址,遗址出土物均为纯正的后石家河文化而不见土著白庙类型文化遗物;同时期的长阳香炉石遗存,两类遗物共出;峡区宜昌白庙遗址也是如此。
上述案例揭示,清江口一带在早期青铜文化中具很高的战略地位,外来“先进”族群往往倾向于在清江口定点,安营扎寨而后向武陵地区腹地进发。有“楚之西塞”之称的荆门山和虎牙山为西北部屏障,清江口一带的战略重要性或与今宜昌相当,因为清江口水陆路交通和可以通达、亦可封锁通往武陵地区腹地、长江上游、澧水流域等广阔区域。
2, 澧水流域
先秦两汉时,澧、沅、资、湘水各自汇入长江,与今澧、沅、资、湘水均流入洞庭湖而后汇入长江的形态迥然不同。由于自然地理的差异,三代时期澧水流域文化可明显分为上、下游两块。下游区与江陵、松滋、公安一带关系较为密切;上游区则与清江腹地、酉水流域面貌接近。
澧水流域商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名“石门皂市上层文化”,皂市遗址中有较丰富的商文化因素,土著文化因素的炊具为鼎,文化属性上与同期武陵地区大部以釜为主要炊具的文化有质的区别[i]。而目前考古界的共识是:商至秦时期,巴蜀族群的炊具以釜为主;越系族群炊具以鼎为主;北方系族群炊具以鬲为主。
值得注意的是,松滋汪家嘴遗址不见商文化因素,却与澧水同期遗存土著文化因素有强烈的共性。发掘者认为这是澧水遗存社会结构复杂化的表征,即高等级聚落接受更多的“先进”文化,低等级居民保持本族群特征。
由于自然地理的高度同质性,澧水上游商西周文化与鄂西、三峡同期考古学文化有更多的共性,而与澧水下游差异较大。主要遗址有桑植朱家台、鹤峰刘家河遗址,酉水有永顺不二门遗址。这些遗存与江汉—洞庭湖区商周文化不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而与峡江及鄂西山区相近,二里头文化时期炊具主要是平底罐、商为釜、西周晚至春秋鼎釜与鬲同出,战国则主要为楚文化鬲。有人认为,西周晚期楚文化对湖南的渗透从澧水开始,对湖南的自觉开发在春秋早期,范围仅限于澧水流域,春秋中期及以后才向今洞庭湖东岸、湘中、沅水酉水等逐步推进。
综上所述,可以有两点认识:第一、先秦时期长江三峡不能通航的状况,决定了在动荡分化改组的三代时期,峡江的战略地位不太高。此时的峡江出口在“楚之西塞”的荆门山和虎牙山,战略要地当在清江口一带。第二、清江口与松滋、公安和澧水一带,是楚人最早着手经营的区域,为楚国京畿的后方,很可能是战国晚期楚之江南地。《史记·秦始皇本纪》“江南十五邑”的地望当符合两个条件:一在自然地理上位于江南、并距楚郢都核心区不远;二在人文心理上与楚族文化有高度认同感。上述清江口至澧水下游的地理位置、考古成果所揭示的物质文化及所透视的精神文化的证据,都是其他区域无法比拟的。
[i] 王文建. 商时期澧水流域青铜文化的序列和文化因素分析[M]//俞伟超主编. 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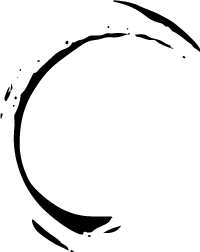
三、联网成区
有道是文化即人的创造成果,它是与自然相对而言的。研究考古出土文物,透物见人乃题中应有之义。所以,我们在探究这个特定历史时空的情景时,不妨聚焦身处江湖山岭中的人群,心怀超越“民族”、侧重“人与自然”层面的思考。至于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研究,则在一定程度上需依赖文献。我们以为在方法论方面何驽的见解值得借鉴:“文献资料绝非局部地、片段地同考古资料相对应,而是相关文献的逻辑关系同有关考古资料的存在背景关系总体对应”。“文献的正确逻辑关系同相关的考古存在背景关系总体的系统性对应,是文献考古方法论的精髓”[i]。此话提醒我们,研究史前时代,以代表性器物命名的文化远比以族命名的文化来的精准。
纵横交错的水陆通道联成网络,是武陵地区这个地理单元中人员与文化内外互动的基础。以下让我们借机在此基础上再探讨一点学术问题。
晚近关于“民族走廊”的讨论起于费孝通[ii]。李绍明在一些论文里对此做过介绍,并且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武陵民族区若从费老板块与走廊学说而论, 它系一个板块, 而非走廊。因为它并不具备民族走廊的地理特征, 从而具有相对稳定性。当然, 并不是说这个板块之中没有通途, 因为从古到今, 板块与走廊均与外地交通相连的[iii]。而且,李绍明还认为,“某一或某些民族长期迁徙的路线必须在特定的自然地理的走廊环境中,始可以称之为民族走廊。……泛民族走廊的说法是不可取的”[iv]。
具体到武陵地区的民族研究,黄柏权曾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民族分布与互动有细致的梳理[v],不过他采用的是“走廊”的概念。他还根据河流和武陵山脉的自然走向, 把“武陵民族走廊”分为沅水、酉水、澧水、清江、乌江五条通道[vi]。
通过以上对武陵地区北部上古交通网络的阐述,我们觉得把武陵地区看作一个“历史民族区”要比称其为“武陵民族走廊”更加合适。“历史民族区”原是民族学苏维埃学派的概念,指“一个由于共同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长期交往和相互影响而在居民中形成类似文化生活(民族的)特点的人们居住区”[vii]。
作为一个历史民族区,武陵地区山高水恶、地势险峻,交通不便,不易形成大规模的聚落,散居和封闭成为本区社会的常态。三代-秦时期本区经历了多次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过程,是多族群间频繁互动、竞争的重要历史时期。该时期遗址的数量,约为古代文化遗址总数的四成,是文化发展的高峰期。不过,此时期的开放和繁荣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种例外。战国至秦时期本区在名义上已先后归属楚、秦政权,从此成为国家政权的“内地”。 秦人对本区的统治,在物质文化上反映不明显,可能更多是在军事、政治结构上的统治。秦汉及后世统治者采取羁縻政策,但仍“时有宼乱”。割据时期的南北朝尤甚,“群蛮”处于“无君长,不相统属”的状态。统治集团对此束手无策,更谈不上有所控制。这是中华帝国腹地一个充满了“空隙”的“边陲”。五代初“溪州之战”后,地方王朝当局者意识到应“树其酋长,使自镇抚”,本区逐渐形成世袭数百年的大姓世家。以后几百年的土司制度,虽说“汉不入峒,蛮不出境”,但土司们却是汉文化的传播者。清初“改土归流”让武陵地区敞开门户,在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方面迈开大步。不过,尽管基本实现物质文化的一体化,本区仍存在许多自身独特的文化元素、风俗习惯和礼仪。武陵地区就是这样一步步行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道路上。
[i] 何驽.文献考古方法论刍议[J],华夏考古,2002(1)。下划线为引者所加。
[ii] 费孝通.关于我国的民族识别问题[J]. 中国社会科学,1980(1).
[iii] 李绍明.论武陵民族区与民族走廊研究[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
[iv] 李绍明. 藏彝走廊研究与民族走廊学说 [J]. 藏学学刊,2005(2).
[v] 黄柏权.先秦时期“武陵民族走廊”的民族格局[J],思想战线,2008(3);黄柏权.秦汉至唐宋时期“武陵民族走廊”的民族格局[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2).
[vi] 黄柏权.武陵民族走廊及其主要通道[J],三峡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6).
[vii] [苏]切博克萨罗夫、切博克萨罗娃.民族·种族·文化[M],赵俊智,金天明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9:2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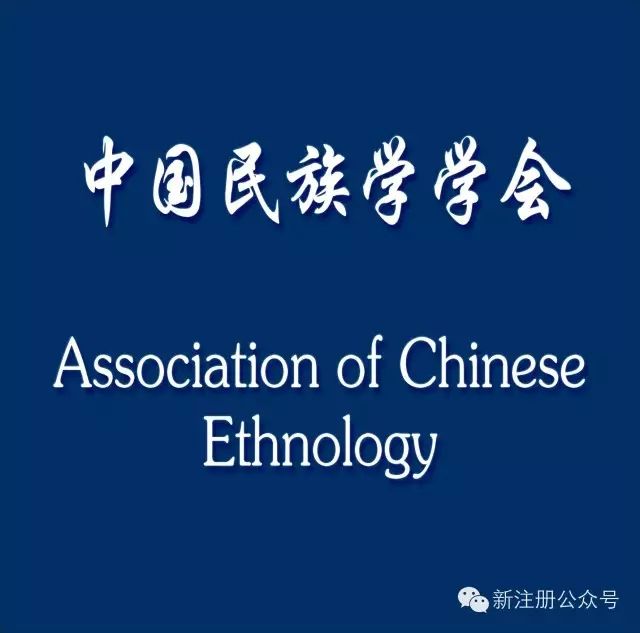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4520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4520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