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论】张亚辉 | 封建、等级与家屋:论林耀华的藏区研究与边政思想
摘要:林耀华先生1940年完成的一系列康藏地区的民族志不但是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以藏区为对象的人类学成果,同时也是人类学家参与边政学思考的重要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林耀华见证和描述了中国边疆封建社会基本结构和正在发生的转型过程,他对封建制度、等级制度和家屋制度的研究迄今为止仍旧是我们理解藏人社会的重要理论工具和思想资源。其中林先生在田野调查中所发现的家屋制度,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已经成为人类学研究社会组织和政治制度的关键观念。本文力求呈现林先生的经验材料脉络和理论思考,以及其中蕴含的边政学主张,以贡献于未来人类学的边疆研究。
关键词:封建 等级 家屋 边疆研究 边政学
1942年,林耀华先生接受成都燕京大学的聘请,出任该校的社会学系主任。1943年到1945年间,李安宅先生和林耀华先生合作主持了一个川康少数民族调研基地,李安宅先生的兴趣一直是藏族研究,而林先生在大小凉山调查结束之后,也于1944年和1945年两年的暑假期间进入康北藏民区域和嘉绒人地区进行了深入的田野调查。1944年,他的田野地点主要在甘孜县城以北的绒擦沟,共11个村庄,调查了50个家户,撰写了《康北藏民的社会状况》[1](1945)。1945年,主要的调查区域在嘉绒四土的范围,即今日理县的西北部区域,发表了《川康北界的嘉戎土司》[2](1947)和《川康嘉戎的家族与婚姻》[3](1948)两篇文章。另外,基于1945年暑假的田野民族志,林先生还撰写了《四土嘉戎》一书,可惜书稿于“文革”期间丢失,我们今天只能够从陈永龄先生相关的藏族研究中看到其核心要旨和被引用的只言片语。1951年,时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林耀华被中国科学院抽调,参加随十八军进藏的西藏工作队,担任历史社会组(后改称社会科学组)组长。这次调查的成果之一是《波密简述》[4]。关于林先生在西藏工作期间的大致状况,王晓义先生曾经在《与林耀华老师及宋蜀华学长在西藏工作队的日子》[5]一文中有简要的叙述。1952年,林先生从西藏返回北京之后,就进入了中央民族大学研究部,任藏族研究室主任。陈永龄先生说:“耀华师之研究目的在于将中国西南各边疆民族作精细之个别研究,然后再同此顺而推及于西北东北各边疆民族及台湾之番民,海南岛之黎民,做一系统之比较研究,则对于未来树立中国边疆民族学之基础殊有贡献。”[6]1964年,林耀华、陈永龄、宋蜀华和王辅仁四位先生联名写了《对我国藏族、维吾尔族和傣族部分地区解放前农奴制度的初步研究》[7],进一步将西部边疆三个典型的封建农奴制社会放在一起作了综合的比较研究。
李安宅先生和林耀华先生是最早进入藏区从事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家。目前学界对李安宅先生的藏族研究成果讨论比较多,而对林先生的田野调查和学术思想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篇系统的梳理性文章。林先生与李安宅先生一样关注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的现代化问题,但由于学术进路不同,林先生的研究自有其鲜明的特色与追求。首先,林耀华关于藏族地区的学术思考与他对大小凉山的彝族地区的研究关系密切,对等级问题格外关注,并且在某些段落中还将两个民族的等级制作了对比分析。其次,林耀华对边疆土司的封建制度更为关注,在这方面,李安宅先生更加注重对寺院庄园的封建制度的分析。再次,林耀华对嘉绒人的婚姻与家名制度作了非常细致的研究,开人类学家屋制度研究之先河,而家名制度直到今天仍旧是我们理解和把握藏族的社会与经济状况的核心问题。这三个方面都跟当时的边疆政治变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其核心的思想则是推动藏民和嘉绒人的政治现代化,尤其是等级主义社会向平等主义社会的转变。《四土嘉戎》书稿遗失,我们已经不可能了解林先生藏族研究的人类学思考之全貌,而《波密简述》由于是在特定环境下写就的文章,其学术思想也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改变。本文将以林先生1944—1945年两次田野调查的学术成果为核心,参照《波密简述》和陈永龄先生1945年陪同林先生调查的学术成果,力求呈现林先生的思想样貌,并和其他人类学家相关的学术成果进行必要的比较分析。
林耀华对康区的考察即包括了甘孜北部绒擦沟的藏人和理县附近的嘉绒人两个群体。这两个群体在祖源上有着明显的区别,在宗教信仰上也有相当明显的差别,康北藏人笃信藏传佛教,而嘉绒人则保留了很多苯教信仰,但两个群体在政治制度、社会组织、亲属制度和土地所有制等方面相似性很高。其中,土司治下的封建土地制度、寺院教区制和家名制度是林先生研究的关键问题所在。
土地与等级
林耀华进入四川藏区进行研究时,正是新国家建制努力抵达边疆的时代,旧有的土司制度虽然还在延续,但总体上已经处于衰败的过程中,新旧两种国家制度都无法有效治理的边疆,成为枭雄辈起的英雄地。林先生沿途几次碰到了被遗弃的土司官寨和同样萧条的农场办事处,末路的旧有封建制度和比较迷茫的现代国家,在林先生看来恐怕都不足以承担边政建设的任务,边政建设,首先得从系统了解边疆社会的整体开始。
康北藏民和嘉绒人当时都处于土司制度治下,林耀华认为这种社会组织方式“半因其地处边区,交通不便而生活方式却保持着原有的封建气味,半因历史上受西藏宗教势力的影响,迄今喇嘛仍居社会上政治上主要的地位”[8]。林耀华并没有严格界定他所使用的“封建”一词的含义,他所说的“封建气味”,核心即指“土司贵族世世袭职,因其拥有领域土地,也就是封建主阶级……平民没有土地所有权,由土司派分田园以作耕种,对土司负有纳粮差徭的责任。”[9]在土司之下,还有世族“吉松”和大小头目,都由土司赐予土地,且不承担任何徭役,但各自都要负责土司政治系统运行中的各种行政工作。平民没有土地所有权,只能耕种土司分派的份地。除了实物地租之外,附着在份地上的还有兵役及各种徭役,据林先生记载,各种乌拉有八种。比平民更低的是科巴,属于土司和头人的私人奴仆,从土司到分有份地的平民都可以拥有科巴。科巴不承担粮差,也没有徭役。关于嘉绒人的土司制度和社会组织,林耀华先生没有正面描述,所述者集中在诸土司的历史沿革、亲属制度和近代头人对土司制度的冲击。从陈永龄先生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嘉绒的土司制度与康北藏人类似,亦区分成土司、头人和百姓三个等级,各级头人有封地,不给土司上粮,不承担徭役,而平民靠份地生存,同时承担繁重的乌拉。林耀华认为,这种极为严重的等级差异是造成当时社会凋敝的重要原因:“村落差户有穷困不堪压迫者,则逃遁他乡到处游荡,或相聚为匪,实行劫夺。人民送子入寺院为喇嘛,大部分的原因亦受经济的压迫。因是作者经历之区,常见村落凋零,人口减缩,破家荡产者比比皆是。许多虚堡空寨表示从前曾盛极一时,今则荆棘满地,野草丛生,不胜荒凉之感。”[10]
牧民以三五牛厂为单位,在一定的区域内放牧,牧场土地亦归土司、贵族或寺院所有。每个游牧区域都有着严格的产权边界,封建主在每个游牧区域设卞卡即头人,来管理牧场和牧民。牧民同样对封建主履行徭役、兵役等义务,越界游牧需要承担所使用牧场的相应义务。牲畜为牧民的私有财产,每年冬季牧民要到低地平坝地区用牲畜交换所需物品。林耀华发现,在农牧民之间存在一种固定的交换联结:“每一牛厂必须觅一农户为主顾,由农户安排厂主的住处,招待厂主饮食,厂主的买卖皆经农户办理交涉,以所得十分之一归于农户以为酬劳。厂主与一个农户发生关系后,每年凡到低地时必以原来农户为主顾。”[11]这样一种代理交易就是牧民唯一能够进入的市场,固定的商人群体在藏民内部没有发展起来,这在林耀华看来是藏人社会无法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林耀华对藏人等级制度的分析主要根据的是土地占有与权力关系。宗教并非林耀华研究的重点问题,但要理解藏人社会的等级制度,必然要将寺院和僧侣团体纳入进来才行。林耀华一方面延续了李安宅对佛教寺院与大学的比较研究,另一方面却说:“康地物质环境困难,历来喇嘛教蔓延,教义消极自守不求进取,甚合人民的心理。”[12]在林耀华看来,喇嘛教除了满足藏人对生前死后之福报的需求外,主要还是作为一种政治经济组织存在的。他说:“喇嘛的势力在康北和在西藏一样,不是限于宗教方面,实际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社会上,喇嘛都操着极大的权力……喇嘛中有越规犯法之事,土司土官又无权过问,所处的地位显见特殊。”[13]政治上,当时刚刚圆寂的香根活佛就是孔撒家土司宜美的胞弟,时任女土司德钦旺姆的叔叔,其权势自不必说。经济上,寺院一方面有自己的土地和科巴,每年除了收租,还要征调科巴为寺院服劳役;另一方面,还设有商号,放贷取息。“多数平民送子入寺为僧,原因由于经济的诱引者为多。凡小儿无论年龄大小经到寺院注册立为沙弥之后,每到半年寺院商号结账之时,必分有红利若干。”[14]
藏人的等级制度还体现在等级内婚制和家屋制度上。等级内婚制指的是藏人和嘉绒人在联姻的选择上高度重视联姻双方的等级对应性,一般情况下都不会接受不同等级之间的婚姻,尤其是土司,如果一个土司希望和头人或者百姓通婚,甚至会招来自己属民的激烈反对。家屋作为土地与权力的载体,亦可区分成土司、头人和百姓三种。土司的家屋之名可以涵盖其统治区域的全部范围,因此也就包含了其治下所有的土地和人口,头人的家屋同样包括自己从土司那里获封的全部土地、人口,而百姓的家屋则只限于自己领受的份地、房屋和家里的人口。
家屋与婚姻
林耀华先生是最早发现和论述家屋制度的人类学家,这一发现被他的学生陈永龄先生所继承,成为分析嘉绒人乃至整个藏人社会的一个十分有力的理论工具。家屋制度后来因为列维-施特劳斯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细致研究而享誉世界。列维-施特劳斯坚定地认为作为一种政治发生学机制的家屋制度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存在十分鲜明的可比性,而林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将家屋制度与封建制度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了。林耀华没有给家屋制度下一个严格的定义,最接近定义的一段表述是:“嘉戎家族为其社会组织的中心。戎人家族没有姓氏,但每家住屋必有专门的名号。这名号的含义甚广,它代表家屋继承人的一切权力与义务,举凡住屋财产,屋外田园土地,粮税差役,家族世系,以及族内人员在社会上的地位等,莫不在住屋名号之下,而有传统的规定。质言之,屋名概括家族团体的物质方面与非物质方面的两重内涵。”[15]在这里,林先生注重的是家屋作为一个封建体的政治和经济内涵,而对构成家屋的婚姻制度内涵则叙述较少。在另外一处,林先生又说:“近亲禁婚之外,其他亲属在原则上皆可联姻。血亲没有族内族外的分别,因是堂兄弟姊妹、姨表兄弟姊妹、舅表兄弟姊妹以及姑表兄弟姊妹,皆一视同仁,平等待遇,彼此之间都可以婚配。”[16]
家屋制度在两个层面上与封建制度有着内在的亲和性。其一是封建主或者领主的权力维系是通过策略性的联姻和继承制度实现的,而对这一政治过程的表述则几乎完全依赖于亲属制度的术语,因此,家屋成为了权力的最重要容器,也就是说,所谓封建,是土地控制权超越了亲属制度,又必须通过后者来表述的政治系统;其二,封建特权,包括劣势特权的分配,以及整个封建体的等级制度和经济运行都是以家屋为基本单位的。对任何一个封建体的家屋制度的研究都要同时考虑作为习俗的亲属制度和作为权力载体的亲属制度两个方面,其实这两种亲属制度都已经被高度政治化,但因为权力作为亲属制度的内在属性所发挥的作用不同,两者的面貌仍旧有着鲜明的差异。
嘉绒人的家屋制度在土司-土舍(获土目)贵族、头人和平民(差巴)三个等级中的表现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考虑到封建制度的等级性,林先生最为关注的是土司贵族的家屋制度,同时由于他在调查期间观察到黑水头人苏永和逐步崛起的过程,故对头人的家屋制度也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关于土司世系起源的问题,林耀华只是简单述及土司远祖来自西藏琼部[17],而没有像马长寿那样去收集整理嘉绒各个土司的祖源神话[18]。尽管中央王朝的册封,尤其是给予土司的印信、号纸对嘉绒人的等级制影响深刻,但本质上,不同等级的人各自据有的“根根”仍旧跟嘉绒人的神话系统有关系。绰斯甲土司家的祖源神话说:远古之世,天下有人民而无土司。天上降一虹,落于奥尔卯隆仁地方,虹内出一星,直射于儴戎。其地有一仙女名喀木茹芈,感星光而孕。后生三卵,飞至琼部山上,各生一子。一卵之子,腹上有文曰“k’rastciam”(绰斯甲)。此子年长,东行,依腹文觅地,遂至绰斯甲为王。人民奉之如神明,莫敢越违……绰斯甲王出三子,长曰绰斯甲,为绰斯甲之土司;次曰旺甲,为沃日之土司;三曰葛许甲,为革什咱之土司。
瓦寺土司的祖源神话说:天上普贤菩萨化身为大鹏金翅鸟曰“琼”,降于乌斯藏之琼部。首生二角,额上发光,额光与日光相映,人莫敢近之。迨琼鸟飞去,人至山上,见有遗卵三只,一白、一黄、一黑,僧巫取置庙内,诵经供养。三卵产生三子,育于山上。三子长大,黄卵之子至丹东、巴底为土司,黑卵之子至绰斯甲为土司,白卵之子至涂禹山为瓦寺土司。
其他几则土司家族的祖源神话大同小异。对这些神话的深入分析不是本文的目的,本文只满足于指出以下几点:第一,卵生总是只发生一次,所有初代土司从卵中孵化出来之后,就会通过婚姻进行正常的人类生育,这使得土司家族的卡里斯马无法通过婚姻与其他家族分享。而且,由于卵的不可分割性,每一辈人中只有一个人被认为是卵的后代,其他人都是胎生的后代,嘉绒人在神话里面就已经确定了每一辈人都会系统地将土司继承人和其兄弟直接划分到两个等级当中,被排斥的兄弟会很快转变成联姻的对象,重新以姻亲的身份被纳入到土司的贵族系统中。第二,不论是喀木茹芈——从她的名字来看,应该是出身于木神家族的女子——还是琼鸟,都只是诞生了三只卵,而将孵化的任务交给了其他人,比如上文中所提到的僧巫。与此同时,孵化的地点变得很重要,两则神话中都说是琼部的山上,而琼鸟和琼部有着相同的名字并非历史原因造成的,而是表明山和琼鸟是一体两面的。琼鸟在神话里和木神家族的女子处于相同的位置,而琼部的神山亦是木族神山,也就是木神的替代物,所以,土司的根根在神话里面就和苯教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个关系是由母系血缘和孵化之地两种因素构成的。第三,这里出现的绰斯甲、瓦寺、沃日、革什咱等土司的名号都是家屋的名字,这些家屋都是琼部神山的模仿物,这也就意味着,家屋带有鲜明的母性特征,一个家屋内部是由两种关系构成的:其一是房屋和每个成员的关系,这是一种隐喻的母子关系;其二是由成员之间的亲属制度构成的网络,神话中已经非常明确地说明这个亲属制度是以父系继承为特征的。
林耀华反复强调嘉绒人的阶级内婚制,他说:“与亲属联婚并行不悖者,就是阶级内婚制。戎人实行阶级制度颇为綦严,能够维持阶级制度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就是阶级内婚之制。所谓阶级内婚,乃系男女配偶限定于相同阶级之内,不同阶级就不能联姻。”[19]林先生在这里所使用的“阶级”一词,其真正的含义是等级。事实上,不独嘉绒人,内婚制是几乎所有等级社会的根本特征之一,但在不同的社会,等级内婚制与政治系统相互作用的方式各不相同。嘉绒人的等级内婚制是由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组成的:第一是土司和土舍的通婚所构成的广义父系内婚制,第二是在不同的土司之间、土司和土舍之间建立的父系外婚制。林先生和陈永龄先生的研究对这一区分没有进行详细的分析,这两种婚姻策略的差异,以及嘉绒土司在这两种婚姻制度之间的选择与穿梭,正是理解嘉绒人政治结构的核心问题之一。
在神话之外,所有的土司都是在具体历史条件下获得中央王朝册封的,嘉绒人系统化地降低旁系地位的策略被转变成了对土目和土舍的册封。土舍从源头上讲跟土司是同一个父系世系的不同分支,马长寿说:“土舍本其宗族也,嘉戎婚姻不避同姓。由血统言,土舍似即为土司世代持续之机构。平时供给婚姻之配偶;绝嗣时,则纳子息为继承司位之人。”[20]林耀华说:“土舍原为土司本族,在土内划有较小的治区范围,也可世袭其职。土舍既为土司本族,就同隶于贵族阶级,只是治权与名号稍逊于土司而已,从婚姻关系而论,土舍似即为土司四代持续的机构。平时供给土司婚姻的配偶,至土司绝嗣之时,又由土舍纳子息以为继承土位之人,或以子息入赘土妇。”[21]土司与土舍的联姻无疑是父系内婚制的某种形态,这种婚姻通过拒绝与没有血亲关系的人交换女性和权力,而将权力完全保留在一个世系之内,其情形一如雅典人强调权力系统的父系特征,同时却允许父系甚至同父异母的兄妹通婚,反而限制母系亲属之间的通婚[22]。土舍作为土司的兄弟,首先被从等级上降低成土司治下的贵族,然后再作为姻亲重新与土司建立联盟关系。这种土司土舍之间的联姻由于历史的原因也会衍生出丰富的变形,比如林先生着重研究的四土嘉绒。“理县北部四土,梭磨、卓克基、松冈、党坝各土司,皆祖述于杂谷,原为杂谷土司的土舍”[23],所以,这几个土司以及杂谷于乾隆年间改土归流而设置的杂谷五屯的守备,原本就都来自同一个父系宗族。他们之间的联姻既带有父系内婚制的色彩,又包含了父系外婚制联盟的因素。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巴底、巴旺两个土司之间。而与父系血亲之外的土司家族的通婚则往往是扩大和巩固政治联盟的产物,某些时候甚至带有冒险的色彩。正是这种婚姻形式,从民国时期开始才使得等级内婚制的边界得以松动,苏永和家族的政治野心才凭借复杂的婚姻联盟策略得以深入到土司制度的核心地带。
尽管家屋制度本身是并系继嗣的,但由于嘉绒政治系统本身是男性主导的,所以陈永龄说:“从权力方面言,嘉戎民族多为父权者,而绝少母权者,除非父死后,母为家屋之家长,而具有才干能力者,虽有赘婿在家,亦须听从母方的安排。但实际言之,赘婿在母系母方之家族中亦颇具影响,盖男子始终为主要之经济生产者也,有时其权实在其妻之上。”[24]嘉绒土司的承嗣方式非常复杂多样,但首选的仍旧是父子继承制度。只要有儿子,土司总是把职位传给其中的一个儿子,另外的儿子们或者出家,或者入赘别家,女儿则要出嫁。第二种方式是在没有儿子而有女儿的情况下,选择招赘一个女婿上门。但这不能看作是不分系继嗣,因为女儿的继承权是排在儿子的后面的,所以真正发生的事情是,女方通过出让一辈人的权力,获取下一代的继承人,所以权力实际上是从外祖父经由女婿传递给外孙的。家名制度的优越之处在于,这个通过招赘而诞生的继承人与父系血亲下直接产生的继承人没有任何政治权力和身份上的差异。第三种是在绝嗣的情况下,土妇继承土司权力,如果土妇已经无法生育,则需要通过过继的方式获得一个继承人。一般来说,过继来的孩子都是土司的父系宗族里或远或近的后代,比如末代梭磨土司思良刚王平,就是在上一任土司绝嗣的时候以族人身份过继到土司家屋之中而继承土司职位的。咸丰九年,卓克基土司绝嗣,亦是过继了党坝土司子格山朋。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广义的父系继承制度的表现。而如果土妇尚且年轻,则她通过招赘来执行权力并产生下一代,林耀华先生和陈永龄先生都认为这是因为土妇作为家屋的主人,自然就获得了这个权力[25]。果然如此,则土妇招赘与土司女儿招赘就没有任何分别了。但这个说法与松冈土司的一个个案是相互矛盾的。1928年,松冈土妇,也就是绰斯甲土司的次女察旺拉姆,设计杀死了入赘的杂屯守备的次子高襄,在没有子嗣的情况下,与头人商议迎其六妹察梭巴珠为继女,即将来的土妇,再由察梭巴珠招赘其他土司之子为松冈土司。如果察旺拉姆自然获得了松冈土司的权力,那她就没有必要将自己的亲妹妹认作义女才能辗转完成继嗣之业了。实际上,也没有任何亲属制度上的依据能够说明土司权力可以直接传递给寡居的土妇。寡居土妇招赘最典型的情况是,在作为土司的哥哥死亡而没有后代的时候,已经离开土司家屋的兄弟可以凭借妻兄弟婚的机制重新回到土司家屋,续娶寡嫂并继承土司权力。如丹东土司登龙初娶明正土司女,龙初不寿,其弟坤山即娶寡嫂,继承了土司职位[26]。妻兄弟婚可以自然地延展为侄子续娶寡婶之制,如高襄娶察旺拉姆就是侄子续娶寡婶,乾隆年间,沃日土司哈儿吉死后无嗣,亦是议由其侄纳尔吉续娶寡婶,承继土司位[27]。再进一步延伸,则招赘的范围可以扩大到整个父系宗族。所以,土妇招赘实与土女招赘不同,前者招赘时前夫的父系血亲是有优先权的,土女招赘自然也会考虑父系血亲的优先权,以避免未来孩子的父系亲属的干扰,但在结构上无疑是更加开放的。招赘乃是整个等级内婚制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在下文即可看到黑水头人苏永和最擅长的婚姻策略就是不断以自己和儿子入赘于别家。不论是土司女儿还是寡居土妇招赘,房名的实际所有者都属于未来由这两种女性诞下的孩子,因此这两种女性对家名的所有权是高于入赘者的,但实际的政治经济权柄则操于入赘者之手。与这种制度呈镜像关系的一个案例,是索观瀛的第二个妻子,也就是索国坤的生母,她是党坝噶斯泰克之女。该女去世之后,原定由索国坤前来继承土舍,但索国坤要继承卓克基土司之位,索观瀛即安排三妻关素贞继承了噶斯泰克土舍。这个案例不放在嘉绒人并不陌生的夫姊妹婚的框架下是无法得到解释的。事实上,关素贞是杂谷千总之女,与党坝土舍俱为杂谷土司后裔。第四种继承方式是土司家保留对嫁出去的女儿所诞之子的所有权。这种方式与第二种方式恰成镜像关系,比如索观瀛之所以被卓克基土司官寨请去继承土司之位,就是因为他母亲是卓克基土司之女。光绪十七年,卓克基土司绝嗣时,曾迎请松潘阿坝土司之子恩部索诺木为土司。林耀华先生猜测阿坝土司曾迎请卓克基土司之女,后来的社会历史调查证明,两方确实曾经发生过联姻[28]。
不论用女性还是男性来完成在不同的封建主之间的牵线搭桥,都是封建制度最为常见的手段,政治联盟因此可以用亲属制度的术语来表达。但在嘉绒地区,这两种牵线搭桥的方式内涵并不完全相同。并系继承制度的出现和发展使得权力运作有了独立的空间,等级内婚制和并系继承制度是一体两面的,不论是娶妻还是入赘,男女双方的根根都来自他们各自的父母。这种貌似对称的结构与权力的单边传承之间的矛盾使得任何一个家屋制度的社会都会人为地制造出不对称的因素,以确保男性世系不会被并系继承制度吞没。以嘉绒土司的婚姻来说,嫁出去的女儿和入赘的女婿,不论是在上攀婚、下嫁婚还是在门当户对的土司联姻当中,都要将两个男性世系结合成一个联盟。然而,出嫁女性可以在夫家和娘家之间进行现实的选择,比如索代赓之妹索代玉嫁于杂谷屯守备高承谦,后者得黑水头人允诺,如果成功阻止索代赓继承梭磨土司位,即被拥戴继承梭磨土司位,高随即暗中阻挠索代赓前来继位,甚至在高承谦已经亡故之后,索代玉仍旧与黑水头人联合阻挠索代赓。而男性入赘者则始终和自己本身的父系世系保持着结构性的关联,这一关联看起来远比兄妹之间的关联来得稳固和强大。比如林耀华先生提供了一个甘孜日杂家土司的例子:乌巴家百户之子翁须夺吉入赘日杂家土司女曲梅折妈,生了尼玛兄弟二人。后夫妇不睦,曲梅折妈手杀其夫翁须夺吉,这引起了乌巴百户家的复仇,乌巴家杀死了曲梅折妈和其长子,即尼玛的长兄[29]。又如,松岗土司高襄被土妇察旺拉姆所害之后,亦曾出偿命价4000 两白银。父系世系跨越家名的复仇或索取偿命价的现象说明父系继承制度在并系继承的结构中仍旧维系了稳定的地位。父系世系在权力继承上的优势,同时也必然带来父系亲属之间更加激烈的竞争,所以父系亲属之间的暴力和杀戮也不让人意外,比如乾隆年间的梭磨土司革儿悟在袭位之后就曾杀害了自己父亲沙甲布的次妻阿色,以及阿色所生三个子女。
头人阶层的婚姻制度与土司非常类似,但头人没有卵生始祖神话的支持,其掌握的权力来自土司的分封,亦有世袭之制。由于权力性质的不同,在头人的婚姻形态当中,父系内婚的比例要小得多,反而是姑舅表亲联姻的优先性十分明显。换句话说,头人虽有世袭之制,但权力不如土司那般稳固和不可争议,而是时时处于变动当中,头人与头人之间的联合与争斗便成了这个阶层最为常见的一种政治形态。这种状况与北美洲几个大部落的两个胞族之间的关系有相当的可比性。比如芦花大头人王珍为了垄断已绝嗣之梭磨土司的权力,又恐麻窝头人吉吉不服,便率先发难,在麻窝的水井中下毒。事情败露之后,麻窝杀死了王珍,然后却允诺将女儿益思根嫁于王珍之子旺图的儿子贡达尔,待芦花前来迎亲时,又将芦花人全部屠戮。旺图与麻窝相抗数年,最终却以益思根嫁给了贡达尔而冰释前嫌[30]。至于姑舅表婚,典型的例子就是麻窝头人与木苏头人之间的联姻。木苏头人任贞南毛甲娶麻窝头人吉吉的妹妹为妻,生子高羊平与高丽华。高羊平继承木苏头人之位后又入赘芦花太太益思根,后者是吉吉的女儿。高丽华先是嫁给了吉吉长子苏永清,永清死后,又嫁给了永清之弟永和[31]。两家头人在两代人之间的四次婚姻俱为姑舅表婚,这种联盟关系极大地拓展了两家头人在当地的政治力量。在益思根嫁给贡达尔之后,贡达尔为小头人楚思加所杀,后者联络汉军,支持索代赓代理梭磨土司之职,而益思根则回到麻窝寻求苏氏兄弟的帮助。从索代玉和益思根各自跟自己兄弟的关系,亦足可见土司与头人之权力性质和婚姻方式之差异。
除利用姑舅表婚来巩固联盟之外,上攀婚亦是头人重要的婚姻策略。由于土司婚姻的男性世袭制的约束,头人女嫁于土司子往往对双方都没有什么好处,因为所生之子会直接属于土司家,但此子之母等级地位又显低下,而头人对土司家的舅权受制于等级的差异,也完全无所伸张。但在林耀华先生所见之20世纪40年代,情形稍有不同。苏永和以女格西担珠嫁卓克基土司子索国坤,固然令索观瀛十分懊恼,“索氏常叹国坤惧内,且已露袒护岳家之心”[32],索观瀛甚至直接传位国坤,自己入赘党坝土妇,但当看到国坤纳土司印信于格西担珠,卓克基头人亦渐为后者收买时,又从党坝回来收回了土司印信。格西担珠之所为与其姑姑益思根如出一辙,但其对苏永和伸张势力之协助更多来自其个人的谋略胆识,并不是结构性的因素,最终格西担珠的政治活动空间仍旧为索观瀛收回了。土司子入赘头人女更是完全不会发生的事,所以真正有效的上攀婚往往是头人子入赘或娶入土司女或土妇。林耀华记录了三个个案,其一是党坝土司色林乌是党坝土妇泽朗海与头人恩保彭楚所生,其二是丹东土司登坤山将自己哥哥所遗之女嫁于革什咱头人巴登,其三是苏永清之子苏希贤入赘松岗土妇察愣巴珠。这种婚姻在衰落之土司与有力之头人看来是双方得利的,头人的父系世系因此得以获得土司根根,而土司家则用后代等级的部分衰落来换取强势头人的支持。头人上攀婚最为成功的方式乃是头人女与土司或者土司子偷情,此时所生之子诞生于母家,土司家不会来争夺孩子的所有权,而所生之子未来在头人的竞争中因为具有了土司根根而倍显优势。党坝土司色林乌在婚前即与党坝某头人之女私通生二子,一子名三朗恩波,一子名依布牵牵,这二人后来的情况目前没有文献资料可以说明。苏永和从苏永清那里继承的妻子龙坝太太峨兹密即其母与梭磨土司私通而生,峨兹密本身就是“尊称土司女之意”[33]。苏永清之子苏希贤得以控制来苏下五沟之地,亦与龙坝太太之出生与威望有关。在近代头人政治兴起的过程中,入赘是最为重要和成功的策略,单是黑水头人一家,苏永清、苏永和和苏希贤,就总共上门入赘四次。其中苏永和第二次入赘到松潘毛牛沟,娶土官陈仁清遗孀毛牛沟太太绿歌,已经突出到了梭磨领土之外,进入松潘地界,而唯一一个入赘到土四家的就是苏希贤。相反,苏永和嫁女到卓克基土司家和将龙坝太太次女嫁于甘坡屯守备桑梓侯之子,看起来都收效不大。
至于平民阶层,则政治权力的影响力愈发式微。陈永龄先生的调查表明,父子相传虽然仍旧是通常的继承方式,但喇嘛打卦对于具体选择哪一个子或女来继承房名,哪一个出嫁或者入赘都有更强的影响:“如一家有一子一女,普通多由子传代,女出嫁,如经看卦后,子须出家做喇嘛或须外出入赘上门时,则留女在家招赘婿,亦传该房后代。”[34]在平民阶层,姑舅表婚仍旧占有优势,但父系和母系的平表婚也都是允许的,权力因素的减弱使得父系亲属不再有计划地排斥旁系或优先通婚。但这并不意味着平民阶层的家屋制度是完全对称的并系继承制度,如果婚姻形式是娶妇的从夫居,新妇在生育之前往往是长住娘家的,直到第一个孩子降生后才会长住夫家,而入赘的婚姻则要求新郎在结婚仪式之后马上就开始长住妻家。
为了理解平民的家屋制度,我们可以尝试对构成嘉绒人家屋制度的几个因素区分开来进行分析。首先,住屋的财产可以区分成动产和不动产,女儿出嫁、儿子出门入赘时都会带走一部分财产,真正不可分割的只有土地和房屋。每个平民的家屋都领有固定份额的土地,除了特定的群体如土司和头人的科巴外,这些土地都负担着明确的实物地租、兵役和劳役,这些封建义务的固定化显然是对土司的整个封建政治制度的运行更加有利的。而且,这并非嘉绒人或者藏人独有的,份地或者封土的不可分割性是很多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比如早期的欧洲的封土就是不可分割的[35]。所以,每一次继承时,家屋里面只保留一个子女,每一辈人中,只能保留一对夫妻关系,这并非一种文化选择或者自然的亲属制度类型,而是由封建制度决定的。其次,并系和不分系继承制度,其核心问题在于家屋可以由女性继承,而非限于父子相传,这完全是受封土地的世袭原则高度发展的结果。换句话说,当收回封土对封主没有什么好处而只会带来混乱,受封者又强烈主张封土的世袭性时,分封制度的稳定性就变得十分关键,只要封主能够确认受封者有能力完成地租和劳役,并确保后者的效忠,女性继承人的出现就是可以接受的。同样,在欧洲的封建社会里,女性继承人的出现亦是与封土的世袭财产化直接相关的[36]。再次,嘉绒人的婚姻是极端的短交换形式,这使得“与之交换的亲属”的范围极端扩大,而“与之分享的亲属”范围变得极其狭窄[37],婚姻关系因此就超越了继嗣关系而成为亲属制度的核心,封地与家屋也便超越了血缘,成为社会组织的核心,在平民当中尤其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婚姻当中两性是完全对称的,家屋中最重要的家神是灶火,而锅庄中的三脚铁架则总是来自妻子的嫁妆,也就是母系相传的,是最初领受封地或份地时土司赐予的。因此,可以说在嘉绒人的家屋中,权力本质上是沿着男性传递的,偶尔也需要借用女性来度过缺乏男性继承人的关口,而家屋的宗教价值则是沿着女性传递的,嘉绒社会两性的功能分化由此可见一斑,而一个家屋总是由权力和宗教价值耦合而成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解释了新妇在生产之前不落夫家的原因——灶火沿着母系传递,一家只有一个灶火,一个女性无法加入她丈夫的母亲的灶火,只有在获得了一个继承人之后,女性才能将自己的灶火带入夫家,并确保这灶火不会熄灭。
结语:从等级到平等的转变
中国边疆社会近代变革的核心问题即是从一个基于封建制度的等级主义社会转变成一个基于现代性的平等主义社会,林耀华的藏区民族志研究在国家以革命的手段改变边疆基本社会制度之前,看到了藏人社会内部变革的动力学和社会学机制。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是,头人阶层的马基雅维利式的实利主义政治的兴起,给暮气沉沉的土司制度带来了强烈的冲击,梭磨土司所遗之印信再无法让苏永和成为下一任土司,而不过是给他的政治野心一个明确的目标罢了。在头人的冲击之下,素与汉人关系密切的土司便想到要引入现代国家的力量甚至袍哥的力量予以对抗,以便在混乱的局面中取得暂时的优势。这一过程最明显的后果就是等级内婚制的衰落。不同等级之间的通婚逐渐增多,等级制本身便岌岌可危,土司制度也便逐渐失去了再生产的可能性。由于革命的原因,我们无法知道这一过程如果持续下去的结果,但可以确知的是,藏人社会等级制的衰落不乏内在的动力。而正是芦花头人王珍、苏氏兄弟看到土司制度的乏力而兴起的政治野心,使得嘉绒人的政治学逐渐脱离了封建制度的框架——禁忌首先是从内部被打破的。
于式玉1943年曾经见到了苏永和,并且借住在他的头人官寨里面。在《麻窝衙门》一文中,于式玉详细描述了苏永和审案的过程:“他见诉讼人那种不胜惶恐的样子,等他说到一段落,便借机哈哈大笑起来,因为他的笑,满屋同时哄然大笑起来。趁着空气的松动,他便命娃子拿出咂酒来赐予告状的人,由这种方式缓和了他们恐慌而紧张的心理,同时使他们感到头人的和悦可亲……苏永和能给他们咂酒喝,能向他们——并同他们哈哈大笑,这大概是能统帅黑水的最大原因了。”[38]我们可以把这段描述和陈永龄对卓克基土司的描述进行对比:“土司平日皆深居简出,其日常活动亦多限于土司官寨中。是故嘉戎民族,其在上之土司阶级与在下之平民阶级乃是彼此隔绝。在长久隔绝的生活中,百姓永远不能了解土司,对之总是莫测高深,而此隔绝的生活亦足使土司高高超越百姓之上,发号施令,得以维持其威势不衰。”[39]等级制度当然没有在头人的冲击下彻底崩塌,甚至直到今天仍旧在以某种方式延续,但苏永和所主张的政治形式与土司们有着天壤之别。
林耀华20世纪40年代的藏区研究所忧虑的是旧国家的退却与新国家的无力所导致的边疆去国家化,土司与头人之间的混乱厮杀使得嘉绒地区硝烟四起,民生凋敝。林耀华和陈永龄都对土司政治的停滞保守,以及贵族与平民之间巨大的贫富差异十分不满,尤其是平民所承受的沉重劳役让林耀华无比同情而又无奈。在这二位先生看来,边疆社会的现代化和再度国家化完全是同一个问题,“首先我们必须有一个富强康乐民主进步的新中国,然后我们才能看到一个富强康乐民主进步的新嘉戎社会”[40],陈永龄此言亦是林耀华的心声。
参考文献:
[1]林耀华.康北藏民的社会状况[C]//林耀华.民族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2]林耀华.川康北界的嘉戎土司[C]//林耀华.民族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3]林耀华.川康嘉戎的家族与婚姻[C]//林耀华.民族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4]林耀华.波密简述[C]//林耀华.民族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5]王晓义. 与林耀华老师及宋蜀华学长在西藏工作队的日子[C]//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编.中国民族学纵横.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6][24][34][39][40]陈永龄.民族学论文集[M].台北:财团法人子峰文教基金会弘毅出版社,1995.326-327.357.358.372.436.
[7]林耀华,陈永龄,宋蜀华,王辅仁.对我国藏族、维吾尔族和傣族部分地区解放前农奴制度的初步研究[J].历史研究,1963,(3).
[8][9][10][11][12][13][14][15][16][17][19][20][21][23][27][29][30][31][32][33]林耀华.民族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367.368.372.374.379.367.386.412.422.394.425.161.426.396.423.375.399-400.402.406.403-404.
[18][26]马长寿.马长寿民族学论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35-140.162.
[22]列维-施特劳斯.遥远的目光[M].邢克超,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99.
[25]林耀华.民族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424;陈永龄.民族学论文集[M].台北:弘毅出版社,1995.357.
[28]《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四川省阿坝州藏族社会历史调查[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142.
[35][36]冈绍夫,弗朗索瓦.何为封建主义[M].张绪山,卢兆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76-178.179-181.
[37]列维-施特劳斯.人类学讲演集[M].张毅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95.
[38]于式玉.麻窝衙门[J].边政公论,1944,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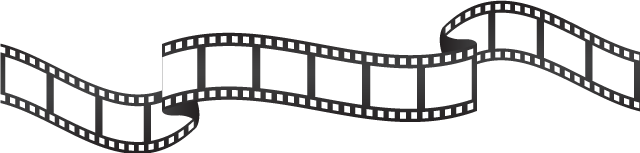
来源:西北民族研究;美编:雅宁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4520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4520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