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声】张雨男 | 鄂伦春族日常生活节奏的变迁与适应
原文发表于《民族研究》2018年第3期,注释和参考文献删去。引用请务必以期刊发表版本为准。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下载pdf全文。

鄂伦春族日常生活节奏的变迁与适应

摘要:近年来,鄂伦春族的生计方式出现了由游猎到定居农业的转变。在此过程中,以资源快速消耗、与猎物生长周期同步、群体活动中穿插个体活动的传统日常生活节奏,逐渐转变为以剩余不断积累、与农作物生长周期同步、以家庭为运转单位的农耕节奏。鄂伦春族在应对禁猎和农耕的外来冲击中出现了问题,世代狩猎生活所形成的节奏难以适应农业生活所要求的节奏,这是禁猎转产以来部分鄂伦春族群众陷入生存困境的深层次原因。
关键词:节奏 日常生活 鄂伦春族 游猎 农业

一、问题的提出

以游猎为生的鄂伦春人早期生活在我国东北大兴安岭腹地。后来,一部分鄂伦春人不断南迁,到达了今天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境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鄂伦春经济社会出现了空前发展。1951年10月,鄂伦春自治旗成立。从1951年到1958年,在鄂伦春自治旗政府的帮助下,习惯于游猎生活的鄂伦春族逐渐实现了定居。为了应对大兴安岭外来移民过度狩猎对当地生态平衡的破坏,鄂伦春自治旗政府于1996年颁布《禁猎通告》,从此鄂伦春族也不得不“弃猎从农”。
近年来,鄂伦春族的生计方式处在由游猎不断向定居农业转变的过程之中。在此过程中,部分群众因未能较好地适应这种转变而陷入贫困。查干姗登的研究表明,转产政策使得相对平等同质的鄂伦春族群体出现分化。何群进而指出,部分猎民转产失败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本文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试图从日常生活节奏变迁的新视角进一步揭示1996年全面禁猎以来鄂伦春族面临的生存困境及其深层次原因。
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晚年将研究重点放在节奏概念上,节奏研究构成其日常生活批判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注意到社会秩序、节奏与身体之间的关系,认为社会秩序是通过一定方式调节活动的节奏,并将其深深烙印于身体之上。 换言之,社会通过对节奏的改变来控制身体,实现对人的控制。此外,节奏也是社会秩序在人类行为上的一种表达。从在身体上观察到的节奏入手,可以探究社会,亦可以了解个体。在笔者看来,日常生活节奏如同布迪厄所言的惯习(habitus)一样,是一种外在客观结构在个体身上的内化与表达,是一种无意识的生活实践。日常生活节奏的产生及其所引发的行动,全部基于生活实践,通常不假思索但符合规范。日常生活节奏是透视文化和社会习俗的一面镜子,由此可洞悉日常生活背后所隐藏的社会结构与文化特征。
在人类学经典研究中,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和贡纳尔·哈兰(Gunnar Haaland)运用节奏视角给出了深入而精彩的分析。莫斯发现,爱斯基摩人的生活在冬夏两季差别明显。在一个年度周期中,从冬夏两季的生活节律来看,爱斯基摩人的社会生活以一种规则的二分节奏交替进行。莫斯的研究呈现出一个社会在年度周期中的节奏变化,而贡纳尔·哈兰对富尔人与巴加拉人边界变化的研究则展现了在同一时空下当地人与生产方式相关联的日常生活节奏。
本研究的田野点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境内的一个猎民村——小河村。村民都是登记在册的猎民。1996年全面禁猎以来,小河村村民(猎民)中有一部分人的生计方式转向农业生产。目前,小河村村民共有70户、197人,其中鄂伦春族157人。该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与外界有较多的交往和交流,同时也保留了一些鄂伦春传统特色文化。小河村现有耕地一万余亩,其中村集体耕地近千亩。据有关统计,该村无地户45户,占全村总户数的64%;有地户25户,占全村总户数的36%。2016年7月至2017年底,笔者先后三次进入该村进行田野调查。文中凡未明确注出出处的材料,均来自上述田野调查。

二、传统日常生活节奏

历史上的鄂伦春人,祖祖辈辈以狩猎为生,形成了以狩猎为核心的传统日常生活节奏。
(一)资源快速消耗
人类学将狩猎采集群体的组织形式称为“游群”(bond)。为了与所处自然环境保持某种动态平衡,这类群体经常游动,普遍缺乏存储行为和观念,私有财产观念不够强烈。习惯于游猎生活的鄂伦春人大体上也是如此,尽管他们有过定居狩猎的阶段。事实上,由于常年需要迁徙,他们对食物资源的消耗节奏较快,很少积累和存储剩余产品,因此没有形成存储行为和存储观念。猎人打猎归来后,会将猎物尽快分食。这一行为不仅与群体生活方式息息相关,也与猎物不易保存,需要快速及时利用和消耗有关。
笔者调查的小河村有集体土地和集体山地等资产,村委会定期分给村民一些红利。村委会给没有正式工作的猎民每人每年分红达到1000元以上,分红时间都在春节前几天。当笔者问及为何在这个时间节点进行分红时,村干部这样回答:
这是因为要是提前发的话,这些贫困户等不到过春节就会花完。这笔钱是让他们置办年货的,这样他们可以过个好年。
这种状况是鄂伦春族传统上普遍缺乏存储观念的一种反映,也是资源快速消耗的生活节奏的一种表现。无论是一万元还是一百元,他们都会很快花完,不种地的猎民向种地户借钱的事情时有发生。很多猎民一开始不会经营现代农业,转产以后的生活面临一些困难。为此,鄂伦春自治旗政府给没有工作的猎民每月发放低保补助金。有些人在补助发放之前的几天,就开始向其他村民借钱度日。这种情况的出现,与鄂伦春族以往所形成的资源快速消耗的生活节奏有一定的关联。
(二)与猎物生长周期同步
鄂伦春狩猎文化是在对他们生存于其中的生活世界的不断认知中形成的。生活世界的整体性及其形塑出来的狩猎生活节奏贯穿在鄂伦春人狩猎生活的方方面面。以狩猎为核心的传统生活节奏与大兴安岭整体世界中的节律息息相关,与大兴安岭动物(猎物)生长周期同步,由此形成了鄂伦春人的传统生态智慧和打猎禁忌。根据鹿的生长周期,他们只能在三月份的时候打鹿胎,到每年四五月份的时候打鹿茸;野猪只能在冬天打;春天不能猎熊,猎熊要等到秋天;狍子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打的。鄂伦春人的生存智慧是在长时间打猎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符合大自然持续发展的规律,能够维持合理的动物种群数量,以达到和保持生态平衡。这种逐渐积累而成的打猎禁忌,在鄂伦春人生活中慢慢地形成一种打猎节奏。在一年之内,有些鄂伦春人的游猎线路是固定的,他们在自己熟悉的区域内寻找应季的猎物。狩猎禁忌知识所形塑的不仅仅是鄂伦春人打猎的节奏,也影响了鄂伦春人一整年的生活节奏。可以说,传统的狩猎生活节奏深深扎根于鄂伦春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在农业社会,人们需要细心照料农作物;在工业社会,人们需要对时间进行精准把控。比照之下,游猎社会生活处于一种较为自由和随意的状态。据笔者的访谈资料,20世纪70年代的某个清晨,猎民白冰的父亲起床后让白冰烧水。交代任务后,父亲就骑马拿猎枪出门了。由于气温较低,烧水时间比较久。水刚刚烧开,父亲就拎着一只狍子骑马赶回来了。狍子经过处理后直接下锅。父亲出门时,没有跟白冰说烧水是为了做什么,他自己也没有什么期待,不过是临时起意。这种临时起意、没有详尽规划的打猎行为是狩猎采集社会一种典型的生活方式,体现出狩猎采集社会的特有生活节奏。在那个年代,富饶的自然环境决定了当时的鄂伦春人可以延续原初社会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节奏。
临时起意、没有详尽规划、相对宽松自由的生活节奏在今日鄂伦春族日常生活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延续和体现。笔者在小河村的调查见证了这一点。关宏斌是村里公认的巧手猎民。他擅长土建,而非农业生产。在猎民村及其周围的村落,与土建有关的活计都会找关宏斌来做。笔者初入村庄时,关宏斌每天早上坐在家门口的板凳上,一边听着自家音响播放的音乐,一边喝着啤酒跟人聊天。这种情况一连持续四五天,每天从早到晚,除了睡觉、聊天以外就是喝啤酒。带有强烈节奏感的音响有时会一直响到后半夜,隔壁的邻居跑过来替关宏斌关音响时发现他早已进入梦乡。在持续四五天以后,关宏斌开始在村庄周围打工干活,在干活的日子里滴酒不沾。凭借自己的辛勤劳动,他每天至少可以挣一百多元。连续工作几天以后,时而会有人叫关宏斌一起吃饭喝酒,他便不去工作。于是又开始了连续几日一天三顿酒的生活节奏。关宏斌的日常生活就在几天饮酒和几天上工的两种状态中不断循环转换,这事实上构成了一种由个人做主、无所拘束的生活节奏。包括关宏斌在内的一些猎民在村里的组织下,曾到小二沟村落附近领养马匹。由于这些猎民经常喝酒,疏于看管,造成马匹意外死亡,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笔者重返小河村时,关宏斌因为旷工太多而被开除。在笔者调查的猎民村里,像关宏斌这样“自由自在”生活的猎民不在少数。这种生活节奏应为过去鄂伦春狩猎生活节奏的惯性使然。
(三)群体活动中穿插个体活动
在传统狩猎时代,鄂伦春人以群体式生产生活方式栖居于自然世界之中。大多数情况下,鄂伦春人会采取集体外出打猎的方式,有很强的平均主义和群体意识。狩猎结束回到“乌力楞”后,要把猎物分给老年人和丧失打猎能力的人,这样就不会出现有人挨饿的情况。类似打猎的群体行为及其对应的群体思维方式在猎民的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何群对鄂伦春酿酒文化作历时性研究时发现,不管是一家酿制的还是几家合作酿制的,都是全“乌力楞”的人一起喝,直到全部喝完为止。传统上,鄂伦春以“乌力楞”作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构成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的统一体。改革开放以来,以“乌力楞”为中心的群体式生活节奏和生活方式开始陷入困境。一部分猎民响应旗政府号召开地,另一部分猎民没有开地,依旧上山打猎。在禁猎以后,没有开地的猎民失去了自给自足的生活来源。当笔者问及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八十年代他们为什么没有开地时,一位老人这样告诉笔者:
打猎时,土地都是按部落划分的,不同部落有不同的狩猎范围。当时忽然要自己开地自己种,就没有当回事。
由此还可发现,鄂伦春族依然习惯于以群体式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时至今日,村民们喜欢相互串门,到别人家一起吃饭喝酒。群体式生活方式在当今鄂伦春族日常生活中也有一定程度的体现。
在传统习俗所规定的打猎时间范围内,鄂伦春猎民上山狩猎的具体时间也是因人而异的,他们也存在个体外出打猎的情况,上文所述的白冰父亲清晨打猎即是一例。在传统鄂伦春社会中,大多数单独狩猎的鄂伦春人都是在群体狩猎之外的空闲时间中进行的。个体单独狩猎主要是为解决在驻地附近临时获取资源的问题,一般不在外宿营。也有一些猎手,因家中有老幼病残需要照顾不能离开或马匹不易跟上群体的行动,不得不长期进行单独狩猎。有些打猎技术高超的鄂伦春猎人不愿意以群体为单位进行外出打猎。赵复兴1957年在托扎敏调查时听当地老人说,曾有个鄂伦春哑巴,打猎技术高,能在险要的山地环境中追捕野兽,有时一人能获取十几只鹿。但他不愿意集体出猎,甚至连家人也不愿意带。周围的鄂伦春人对这种人印象很差,也不愿意和他们一起出猎,认为他们自私自利。在群体狩猎的空隙中单独打猎,则被认为是一种正常现象,不会遭到质疑。这也充分说明狩猎过程中存在群体与个体的切换逻辑及其内在的社会规范要求,展示出传统上鄂伦春人注重群体生活、群体活动中穿插个体活动的日常生活节奏。

三、日常生活节奏的变迁

狩猎采集的传统生产方式塑造了鄂伦春人以资源快速消耗、与猎物生长周期同步、群体活动中穿插个体活动的传统日常生活节奏。在“禁猎转产”过程中,鄂伦春族传统日常生活节奏与农业生产所要求的生活节奏发生了冲突,或者说,他们在应对禁猎和农耕的外来冲击中出现了问题。
(一)从资源快速消耗到剩余不断积累
从狩猎到农耕的转产过程对鄂伦春人的观念和生活节奏提出了新的要求。与作为“即时回报”(immediate return)系统的狩猎采集不同,作为“日后回报”(delayed return)系统的农业生产,需要经营者持续不断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对于习惯于资源快速消耗的鄂伦春族而言,一方面他们不熟悉、不习惯这种人力、物力和财力持续投入的生产方式,缺乏足够的农业生产经验,另一方面也缺乏农业生产所必需的需要不断积累才可以得到的原料和机械。因此,总体来说,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的意愿较低,纷纷将土地转让出去。另外,从狩猎到农耕的转变过程中,鄂伦春族因缺乏存储行为和观念还诱发了一些社会问题。
在当地,人均耕地面积较大,地势平坦,农业生产需要借助机械来提升效率,以节约劳力成本。拖拉机成为当地现代农业生产的标志,过去仅靠人力耕种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大规模机械化种植、收获,需要不断购置原料和机械,需要不断有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具有存储意识、剩余不断积累的生活节奏是猎民从事现代农业生产的重要前提。如今,能够成功经营农业的鄂伦春家庭都已拥有用于犁地、播种、打药的拖拉机,都有一定的存储意识,初步适应了剩余不断积累的生活节奏。相比之下,也有些猎民没有明确的生产规划、收支计划,形成了无序和随心所欲的消费节奏,这些人很难经营现代化农业生产。在20世纪90年代,小河村给每户分一垧地,每户都有地可种。不善于种地的猎民发现自己经营并不挣钱,于是将土地转让出去,一次性“变现”,再次成为“无地户”。这些没有地的猎民既没有土地,也不能打猎,成为没有自主生活来源的贫困户。一些年长的猎民只能依靠政府发放的低保勉强度日。也有部分猎民通过通婚这种社会结合方式形成团结户和姑爷户,日渐适应了剩余不断积累的生活节奏,从贫困中走了出来。
(二)从与猎物生长周期同步到与农作物生长周期同步
狩猎和农耕这两种生活方式有着完全不同的作息要求。狩猎民族按季节打猎;农业作物对天气条件的依赖程度高,对天气变化较为敏感,需要经营者在较短的时间内抢种抢收。事实上,对于鄂伦春族而言,从狩猎转向经营农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需要从与猎物生长周期同步的生活节奏转向与农作物生长周期同步的生活节奏。作息要求上的变化让很多猎民对农业经营望而却步。大豆和小麦等农作物的生长周期使得猎民无法按照过去宽松自由的生活节奏来从事农业生产。
鄂伦春自治旗地处北纬50度左右,每年的无霜期较短,对作物的播种和收割时间有着严格的要求。一旦耽误了播种或收割,作物容易遇上霜冻,会对投入大量资本的现代农业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一旦错过秋收最佳时机,遇上连续下雨的天气,会影响当季农作物产量,严重时甚至有可能出现亏损的情况。这就要求种地猎民保持与农作物生长周期同步的生活节奏。小河村的种地猎民在农忙时节每天只睡三个小时,凌晨两点起床,开着拖拉机下地播种。为了保障农作物的良好生长,需要从事农业活动的猎民对农业种植节奏有所规划,并严格遵守,而不能随意为之。有些猎民耕种了面积两百亩左右的土地,每年固定要在四月中旬播种小麦,在五月中旬前后播种大豆。由于地块分散,不同地块的先后顺序也需要遵循作物生长的自然规律。每年修理拖拉机的时间则固定在播种小麦和大豆两者之间的间隔期内,小麦和大豆的播种机要在相应作物播种前维修。这些与农作物生长有关的活动形塑了这些猎民的生活时间表,要求猎民形成有规律的、严格稳定的农耕节奏,与狩猎采集自由自在的生活节奏形成了鲜明对照。当然,这并不是说狩猎活动是恣意妄为、毫无节奏的生计活动,狩猎活动同样有自己的节奏和规律。
农业生产活动也需要种地猎民在饮酒上要有相对的节制。鄂伦春人热情好客,喜欢饮酒。在喝酒的频率、时长和数量上,小河村种地猎民要低于、短于、少于不种地的猎民。种地猎民在家喝酒时的规模和人数也要小于不种地的猎民。这种区分与这些猎民从事农业生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于务农的村民而言,必须要对饮酒这种相对自由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娱乐活动和消遣方式有所节制,这是这部分鄂伦春群众对务农生活节奏的逐步适应所致。
(三)从群体活动中穿插个体活动到以家庭为运转单位
随着改革开放和发展农业的需要,经营农业的鄂伦春猎民从群体式生活方式逐渐转向了家庭式生活方式。对他们而言,家庭成为适应农耕节奏运转的重要载体,与传统日常生活节奏运转以群体和个体为载体形成了对照。
传统狩猎采集的生产方式与以“乌力楞”为单位的群体生活方式相辅相成,但这种群体生活方式随着农业生产经营日渐淡出鄂伦春主流社会生活。当然,仍有部分猎民不以家庭为生产单位,未能完全适应现在的农业生产方式,他们不习惯按劳分配的分配方式,也不适应日益商业化的经济和社会。在猎民的日常生活中还能看到群体文化特质,看到具有群体特征的狩猎节奏惯性。这种节奏与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方式难以协调一致。群体式生活中的平均主义,遭到了以家庭为单位“能者多劳”、效率优先原则的挑战。鄂伦春人习惯的群体生活节奏与以家庭为单位的农耕生活节奏构成的矛盾,使得他们无法快速改变节奏,进入到收入较为稳定但要求比较严格的农耕生活节奏中。大多数猎民因没有很好地适应以家庭为单位的农耕节奏,错失开地和发展农业的良机,逐渐对农业经营失去兴趣。
据笔者与当地一些年长的鄂伦春群众的访谈,小河村在1955年开始出现有关定居的宣传,1957年完成猎民下山定居的工作。随之成立的猎民队,从事狩猎、务农、放牧等生产劳动。1960年公社成立开荒队时,购买了五台双轮单犁、两台播种机、七辆大车。开荒时期以集体为单位的农业发展效果不尽如人意,收成欠佳。20世纪80年代,大自然的过度开发使得可供狩猎的空间在日趋缩小,继续坚持这种生计方式的前景并不乐观,狩猎收获日渐减少而且越来越不稳定。猎民每年都需要国家扶助才能生活下去。经过政府的耐心宣传,部分鄂伦春人意识到土地的重要价值。在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政策影响下,一部分猎民开地时大多以家庭为单位,或者采取两家或两家以上合作开地的方式,以五五、四六等分成方式进行收获分配。如前所述,尚有一大部分猎民因不熟悉农业经营、对农业生产没有兴趣、害怕出现毁约等情况而没有开地。
当地人均耕地面积大的特点使得农业生产活动不能仅依靠人力,需要以家庭为单位借助机械来完成,由此也形塑了适应农业生产的猎民以家庭为单位的新的生活节奏。家庭成员在每年的农闲时节,要对拖拉机进行维修,更换零部件。在维修的过程中需要家庭内部成员分工协作,或找村里其他猎民帮忙。此外,因为无霜期较短,在春天播种和秋天收获时要在较短的合适时间内完成作业。在操作机械时,需要有人在土地旁边照看。播种时,要轮流使用机械,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耕种更多的土地。家庭内部要有分工,确保有人在家做饭,为从事种地的家庭成员提供后勤保障,以便让他们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高强度的农业生产作业。在这种情况下,拥有较多劳动力和结构完整的家庭占据一定的优势。经营农业的猎民家庭结构相对完整,破碎家庭所占比例不高。出现了破碎家庭的情况,他们也会很快重组家庭进行修复。另外,达斡尔族和汉族移民通过婚姻方式进入鄂伦春猎民村时,也会帮助猎民村部分鄂伦春群众逐步熟悉农业生产,为鄂伦春猎民带来稳定的适合于农耕节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鄂伦春猎民村内部因农业经营在生活节奏上产生了分化,家庭成为农耕生活节奏得以运转的重要载体。

四、分析与讨论

世世代代以狩猎为生的鄂伦春人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狩猎生活节奏,一种“惯习”。面对“禁猎”与“农耕”的外来冲击,鄂伦春人 的传统日常生活节奏被打破,部分群众因难以适应新的生活节奏而陷入贫困。
首先,对猎民个体而言,很难从以狩猎为核心的传统日常生活节奏快速过渡到农耕生活节奏之中。二者节奏的不匹配使得他们难以适应农业生产经营。其次,就猎民村整体而言,已经逐步习惯于农耕生活节奏的种地猎民与不习惯于农耕生活节奏的不种地猎民在经济生活上的差距越来越大,猎民村产生了社会分化。再次,在鄂伦春猎民定居后生活的区域内部,存在不同的生活节奏。与小河村联系较为紧密的达斡尔族和汉族移民善于农业生产,早已形成了以农业为主的日常生活节奏。部分鄂伦春群众正在逐步适应农耕生活节奏,而有些鄂伦春群众依然困扰于农耕生活节奏。
猎民虽然手中已经没有猎枪,但狩猎生活节奏或者惯习会长期影响其日常生活。鄂伦春猎民周围的务农者在羡慕政府给予鄂伦春开地的优惠政策之时,发现他们不愿开地;当村委会决定分地给猎民时,猎民也不愿意种,而是将土地外租或转让出去。这类事例不断累积的结果,使外界形成了鄂伦春族“懒惰”的刻板印象。外界总以农耕生活方式的立场和视角来想象传统的狩猎采集生活方式,简单地为其贴上“落后”的标签。事实上,鄂伦春猎民面临的问题关涉到一个有关“发展”的问题。“发展”是否存在千篇一律的模式?集约化、大规模的耕种可能带来可观的收入,但猎民们不一定能够很快适应这种农耕生活节奏。对于狩猎采集生计者而言,是否务农和定居即意味着发展?在今天的社会条件下,狩猎活动事实上已经难以持续。问题在于,只有从事农业生产才是唯一的替代出路吗?
鄂伦春猎民日常生活节奏的经验研究不仅可以理解鄂伦春猎民转产过程中面对的困境及其深层次根源,也揭示了社会政策在应对此类民族问题中出现的问题。需要正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不同之处,需要避免做出孰优孰劣的价值判断。在大兴安岭的土地上,汉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等不同民族一直处于相互学习的过程中,他们之间的文化和生活习惯也因此在不断交融。学习与交流的过程是双向互动的,不宜将这些民族置于单向度的梯级进化论之中。不同民族的生存智慧有助于反思习以为常的单向度和阶梯式的发展观念,有助于理解现代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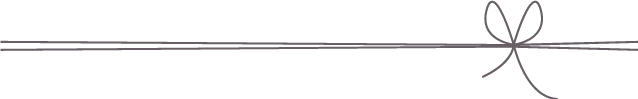
来源:民族研究ENS;美编:雅宁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4520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4520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