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南亚研究】张雨龙:老挝北部阿卡人移居坝区的历程与文化调适 ——勐新县帕雅洛村的民族志个案研究
摘要:在多民族国家中,国家主导的民族地区的国家化进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民族群体欲进入国家体系获得应有的权益也需要付出努力。本文以老挝琅南塔省勐新县帕雅洛村阿卡人这一民族志个案,展现了一个山地民族从政府实施移居坝区政策期间拒绝下山到后来在国家力量和市场经济共同作用下主动涌入坝区的历程。同时,移居坝区的阿卡人在不断寻求经济生活改善的过程中,也在主动进行文化调适,并创造性地继承传统文化,从而融入“文明”进程,并力图在国家化进程中获得更大的权益。
关键词:老挝北部 阿卡人 移居坝区 文化调适 帕雅洛村
在多民族国家中,国家主导的民族地区的国家化进程是旨在强化国家对民族地区及民族群体的管理与控制,并向民族地区传播国家倡导的文化、技术、观念等以促进民族的发展。然而,这一进程通常阻力重重。1992 年至2000 年,老挝政府在北部推行的山地民族移居坝区政策,该政策的目标 就是试图将山区的较少接受国家管理的民族移居到坝区以强化国家管理,同时用坝区的生计方式 和新的文化来育化山地民族,以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政府的良好愿望只是 一厢情愿,在山地民族没有改变旧有的生计方式、国家未能为山地人进入坝区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 提供具体路径的时候,这项政策最终难以执行。从2002 年开始,老挝政府在加大禁毒力度、阻断山 地民族严重依赖的罂粟种植业的同时,大力开展“替代种植”项目,使山地民族看到了在坝区新家 园种植甘蔗、橡胶等作物的希望,也使山民在坝区的打工市场中发现了机会。于是,山区生境的改 变和坝区新市场的形成促使大量的山地民族下山谋求生存与发展。那么,在国家推行山地民族移 居坝区政策期间,拒绝下山的山区阿卡人后来为何又主动移居坝区呢? 移居坝区的阿卡人又如何 进行文化调适以融入国家化进程? 我们通过对老挝琅南塔省勐新县帕雅洛村( Ban Phayalaung) 的 民族志个案研究来探讨这些问题。
一、帕雅洛村:移民聚居村
帕雅洛村隶属于老挝人民共和国琅南塔省勐新县,是一个阿卡人村寨,全村75户388人,除1人是来自中国的汉族(上门女婿)外,其他都是阿卡人。勐新县位于老挝琅南塔北部,距离省城南塔约58公里,与中国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腊县接壤。勐新县城距离中国勐腊县勐满镇24公里。帕雅洛村位于勐新县城东面,西距勐新县城9.3公里,东距离中老边界线约3公里,东南方向距离中国勐腊至老挝勐新通道的老挝班南边防检查站约5.5公里,距离中国岔河检查站约6.5公里,距离中国勐满镇政府驻地约18.5公里。
帕雅洛村因村里的头人“最玛”被佬族统治者封为“帕雅洛”( Phayalaung,地方官员的官衔,负责管理山地某一区域内的若干个村寨)而得名。“帕雅洛”在当地位高权重,故大家把他所生活的村寨称为“帕雅洛村”。1951年前,帕雅洛村位于澜沧江东岸的高山上。1951年,因山区受到国内战乱以及土匪骚扰的影响,帕雅洛村在地方当局的帮助下逃离硝烟弥漫的山区,搬迁到勐新坝子的边缘建立新的帕雅洛村。1962年,生活在中老边界线上的帕雅洛村村民担心边境不稳定,又搬迁到勐老县建立新的帕雅洛,即如今的勐老县帕雅洛村。1987年,勐老县帕雅洛村的富人桑梅带着7户人家回到1951年至1962年间的“帕雅洛村”旧址附近建立如今的勐新县帕雅洛村。
帕雅洛村地处勐新县城附近,在基础设施建设、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受到政府的更多支持和帮助。1994年,勐新县政府与村民共同将帕雅洛村到勐新县城的路修通。1995年,当帕雅洛村自主修建学校后,县政府派老师到村里教书。2002年,县政府将帕雅洛村作为禁毒工作示范点。在政府帮助下,帕雅洛村分别于2006年通水、2010年通电。
在地方政府给予支持和帮助的同时,帕雅洛村阿卡人也努力寻找新的发展机会。帕雅洛村位于勐新坝子边缘的东面,村寨海拔约600米,最高海拔约750米,气候较为炎热,不太适合种植罂粟,适合种植甘蔗、橡胶等经济作物。1997年,帕雅洛村的村长和一名中国老板合作种植甘蔗,同时为了解决劳工短缺和劳动力素质差的问题,他们俩帮助帕雅洛村的村民戒毒。1998年,许多戒毒成功的帕雅洛村村民自己尝试种植甘蔗,至今依然有部分村民在种植甘蔗。2004年,在老挝—中国合作开展的“替代种植”项目和中国西双版纳边境村寨大力种植橡胶的影响下,帕雅洛村村民开始种植橡胶。如今,橡胶种植已经成为帕雅洛村主要的生计方式和经济来源。同时,地处中老边界线附近的帕雅洛村利用有利的地理位置优势,发展边境贸易。2002年以前,帕雅洛村村民用中国的日用百货换取老挝山区阿卡人手中的鸦片、野兽干巴( 野生动物的肉切成块用烟熏制成的肉干)、动物皮革、珍贵药草等倒卖到中国境内。2002年后,老挝政府修通了通往每个村寨的公路(土路),山区人可以自己到坝区购买日用百货并出售山珍野味。此后,帕雅洛村阿卡人主要是从山上采摘一些野菜、野果带到中国勐满镇的集市上出售,这构成他们的一项主要经济活动。
2002年以前,帕雅洛村的人口增长较为缓慢。帕雅洛村的人口从1987年的7户47人增长到2002年年初的25户117人,帕雅洛村因不到30户而面临被合并到其他村的危险。但2002年后,作为禁毒工作示范点,政府在帕雅洛村基础建设方面的投入是很大的,在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之后,该村种植橡胶和甘蔗的自然条件及市场条件等优势得到很大的凸显。大量的山区阿卡人在看到这些优越条件之后,陆续迁入村寨。2013年8月已经增加到75户388人。目前,帕雅洛村由来自勐新县和勐老县的7个村寨的阿卡人组成。分别是:勐新县帕雅洛村人、勐新县阿甲迈村人、勐老县缅控村人、勐老县嘎切村人,还有3户村民来自不同的村寨。如今,帕雅洛村已经成为一个较为典型的山区移民聚居村,这些山区阿卡人迁入帕雅洛村的过程可视为老挝北部山地民族阿卡人在看到发展的新的机会而移居坝区历程的缩影。
二、发展受阻:山区阿卡人拒绝入村
事实上,阿卡人从山区迁入坝区的过程充满曲折。这原因主要有二:其一,阿卡人习惯于延续多年的“刀耕火种”生计方式,这一耕种方式的传统知识在新的坝区经济生产中失效;其二,在新的生产生活空间中找到发展的路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阿卡人是山地农业民族,过去以刀耕火种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刀耕火种就是以轮歇的方式交替耕种和休闲土地,不断地将休闲土地上生长的植被所贮存的太阳能等能量转换到耕地里的农作物上,实现从天然植物到栽培作物的循环,从而满足人类需要的人类生态系统。……在人口少而资源丰富的环境里实行山地民族传统的环境保护和有规划的顺序轮歇刀耕火种方式,对自然生态环境亦谈不上有多少消极的影响。”老挝北部的山地民族阿卡人就是有规划、有顺序地实行轮歇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他们主要种植旱谷、玉米等粮食作物,并种植少量的棉花、豆类、瓜果等,还在森林中采集野菜、野果以及猎取野生动物来补充食物。阿卡人种植的旱谷、玉米等只是他们的食粮而不能带来现金收入,他们到坝区集市出售牛和猪以换取不多的现金收入。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罂粟种植是阿卡人的主要经济来源。1893年,法国开始对老挝进行殖民统治,并把罂粟这种可以获取暴利的作物带入老挝,然后“建立罂粟种植基地和鸦片收购站,并提供现代化运输工具参与贩运毒品,‘以毒养军,以军护毒’,通过贩毒来为其政权与势力提供强大资金支持。”这样,老挝北部成为了金三角地区的罂粟主产区之一。自从罂粟进入老挝北部山区后,在保证旱谷、玉米等粮食生产的同时种植大量的罂粟成为山区阿卡人的主要生计方式,由此,山区民族的经济来源就这样和不光彩的毒品产业相互关联了起来。
1975年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后,老挝政府就开始尝试了禁毒。1976 年4月,老挝在全国开展了“扑灭社会瘟疫运动”,严厉打击吸毒与贩毒人员,毒品生产与销售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控制。1978年,老挝在联合国禁毒署的援助之下,制定并开展了“毒品作物改植计划”。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老挝政府还多次派出军警,查封北部的海洛因加工厂。由于没有给鸦片种植者提供替代罂粟种植经济的新的发展方式,单纯的禁毒的效果并不理想。山区依然是罂粟种植区,阿卡人、赫蒙人等山民依然继续种植大量的罂粟。
使罂粟种植者离开适宜罂粟种植的土地,使散居山区难以管理的山民进入坝区是长期以来政府实施禁绝鸦片的一种方式。1992年,勐新县政府开始推行山地民族移居坝区政策。主要目的就是让以种植罂粟为生的阿卡人、赫蒙人等离开山区迁入坝区,防止其继续种植罂粟,同时加强政府对他们的管理。勐新县政府还希望这些山地民族的迁入能扩大县城及周边的人口规模,促进县城的发展,也改善山地民族的生活状况。在该政策实施过程中,政府为从山区搬迁到坝区的村寨划拨了土地、打通了公路、修通了自来水。然而,这一在国家看来是有益于少数民族发展的政策的实施却阻力重重。在这些阻力中,山地少数民族如何获得新的发展机会是最为根本的。
在勐新县政府推行的山地民族移居坝区的政策中,居住在山区以种植罂粟为生的阿卡人是主要对象。为了更好地开展山区阿卡人移居坝区的工作,勐新县政府指定在县政府任职的阿卡人梅沃作为负责人。梅沃也认为居住在山区的阿卡人同胞如果能移居到坝区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和出路,于是欣然接受这项任务。1992年至2000年的9年间,梅沃曾无数次到山区的阿卡人村寨做工作,但他的工作成效甚微,在53个阿卡人村寨中,他只说服了一个村寨搬迁到坝区。
在政府实施山地民族移居坝区政策期间,一直苦于如何增加人口数量的帕雅洛村,非常希望借助政府的政策和政府官员梅沃的能力来“引进”山区阿卡人。但是,帕雅洛村失望了,没有任何一个山区阿卡人愿意迁入坝区边缘的帕雅洛村。无奈之下,梅沃从同样是位于坝区边缘的勐老县帕雅洛村“引进”了6户村民。正如梅沃曾感叹的,他的那些努力的最大的成果就是1993年12月,被他说服的妹夫及其他6户村民迁入了帕雅洛村。
1993年发生在村里的一件事情让帕雅洛村人更加感受到因人口少而错失政府的建设项目的痛苦。1993年底,勐新县政府计划在那些有足够的学龄儿童的村寨建立小学。帕雅洛村当时只有18户95人,学龄儿童10余人,达不到政府建学校的要求。所以,政府没有将帕雅洛村纳入建小学的计划中。为了使村内的学龄儿童数量达到政府建立小学的要求,帕雅洛村人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不断地上山邀请山区阿卡人,但结果却是没有一个山区阿卡人愿意迁入村里。政府最终还是没把帕雅洛村的学校建设纳入计划内。1995年2月,帕雅洛村只能以村民自愿捐款、义务劳动的方式修建了一所学校。
帕雅洛村阿卡人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无论怎么盛情邀请,山区阿卡人都不愿意迁入村里。但是,政府官员梅沃的一番话却是道出了阿卡人拒绝下山的一部分理由。梅沃说:“那些阿卡人都是憨包,政府领导那么好心地叫他们下来,给他们土地,帮他们修路,但他们还是不愿意下来。他们说害怕疟疾、风寒等疾病,这些都是借口。你看我也是从山上来的,还不是活的好好的。其实那些山区的阿卡人就是舍不得罂粟,就是害怕到了坝区就要戒毒。”
不可否认,害怕坝区的疟疾、风寒、瘴气等热带疾病也还是阿卡人不愿意移居坝区的一个重要原因。过去,由于长期居住在气候较为凉爽的山区的阿卡人对炎热坝区的热带疾病的免疫能力相对于长期居住坝区的佬族人是非常低的,在过去医疗条件很差的情况下,染上热带疾病就意味着生命危险。在坝区患上热带疾病死亡的一些恐怖事例至今仍存留在许多阿卡人的记忆中。这是山区阿卡人不愿意搬迁坝区的一个重要原因。
也如梅沃所说,山区阿卡人不愿意离开山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他们不愿意放弃种植罂粟的机会。在山区罂粟种植并不需要像种植水稻那样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和时间,还可以获得比种植水稻更好的收益。大部分山区阿卡人也不擅长于种植水稻。也就是说,在长期生活在山区的阿卡人看来,坝区没有比山区更好的挣钱机会。
山地民族对于坝区的拒斥与他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环境中所形成的惯习有关。所谓的惯习“是持续的、可转换的性情倾向系统。”惯习往往与场域联系在一起,即惯习是场域的惯习,脱离场域的惯习也是不存在的。当此场域的惯习碰到彼场域时可能会出现布迪厄所谓的“不吻合”的现象。这或许就是山区阿卡人不能很快适应坝区生活的重要原因。然而,既然惯习是习得的,那么,惯习也就是可以转换的。像政府工作人员梅沃一样早已移居坝区的阿卡人经过较长时间的努力后就已经形成了适应坝区生活的新的惯习。
迄止2000年,勐新县政府推行的山地民族移居坝区政策的失败并不表明山地民族有意反国家化进程或逃避“文明”,而是他们还没有做好接受一种新“文明”的准备。而从国家层面来看,他们当时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铲除罂粟种植,从而断绝这样一种不光彩的生计方式,此外,政府还只是简单地认为主体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可以适合于所有民族,除了安排移民按照主体民族的方式进行生产生活之外,并没有合理的“归化”、“育化”山地民族的制度性安排。
2001年,推行山地民族移居坝区政策失败的勐新县政府开始有计划地修通县城通往每个村寨的公路(土路)。到了2002年,政府已经帮助山区绝大部分村寨都修通了公路。其主要目的是加强政府对山区的管理与控制,特别是对毒品源的控制,同时也是为了便利山区的交通,促进山区与坝区的交流以及山区的发展。
2002年,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辖区居民的管理,勐新县政府计划将一些户数和人口较少的村寨合并,特别是那些不到30户的村寨要坚决实行合并,或者这些人口较少村寨的村民分批迁入到其他人口较多的村寨。由于1993年因人口少而失去由政府出资修建学校的机会的痛苦经历,使帕雅洛村人非常清楚地知道如果人口规模达不到政府的要求,村寨肯定将被合并。于是,为了保住村寨,帕雅洛村的村民们再一次上山盛情邀请阿卡人迁入村里。经过多次上山邀请,村长切波终于在2002年底从自己的老家勐新县阿甲迈村请来了8户村民。帕雅洛村人口终于增加到33户150余人,避免了被合并到其他村寨。
三、人口激增:山区阿卡人涌入村寨
阿甲迈村的8户村民愿意离开长期生活的山区迁入坝区边缘的帕雅洛村,表面上看是他们难以拒绝帕雅洛村人的盛情邀请,而实际上,老挝政府禁毒工作力度的加大、中老合作开展的“替代种植”项目初显成效和坝区的打工市场形成等才是最为根本的原因。
尽管老挝政府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后就开展了一系列禁毒工作,但禁毒效果不佳。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老挝和中国合作开展了旨在消灭罂粟和发展社会经济的“替代种植”项目,但“替代种植”项目的实施范围等也还是有限的。老挝北部琅南塔省在1991年的第五届老挝人民革命党代表大会上将橡胶种植确定为扶贫的策略和稳定“替代种植”政策的方式。1994年,琅南塔省开始种植了少量橡胶。但琅南塔省的勐新县境内直到2002年才真正开展禁毒工作,到2003年才开始种植橡胶。2001年,老挝出台了《老挝2001—2005年禁种毒品计划》(简称“五年消灭罂粟计划”),即计划到2005年6月26日世界禁毒日前夕,老挝全境禁种罂粟。根据5年计划,琅南塔省勐新县于2002年开始加大对山区的禁毒力度。政府的禁毒决心加上刚修通的公路带来的便利交通,使得此次的山区禁毒工作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加有成效。2002年后,绝大部分山区居民都不再种植罂粟,大部分吸毒者都被送到戒毒所戒毒。
丧失罂粟种植这一重要的经济来源后又没有找到新的经济来源,使得阿卡人的经济收入越来越少,生活越发困难。为了维系生活,部分阿卡人也偷偷地种植了罂粟,但都被禁毒工作队发现了,不但所有种植的罂粟被铲除了,种植者还被罚款了,有些人甚至被关入了大牢。偷种罂粟的高风险迫使山区阿卡人只能选择放弃,转而考虑寻找新的发展机会和方式。
此时,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老挝政府和中国政府合作开展的“替代种植”项目初显成效。不仅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进入老挝北部开展“替代种植”项目,而且老挝北部城镇周边的居民也开始种植甘蔗、橡胶等经济作物。到2002年左右,中国的企业已经在老挝北部勐新县城周边建立了许多甘蔗园、橡胶园和香蕉园等,这些种植园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来管理,除了长期的管理工人外,还需要大量的季节性和阶段性的劳工,这为周边的居民提供了大量的打工机会,大量的农民通过到种植园打短工和种植甘蔗获得了较高的经济收入。
此外,老挝政府大力兴建公路的作用开始凸显。便利的交通让越来越多的山区人到坝区出售山珍野味、购买生产生活用品、求学、办事以及走亲访友等,同时也有更多的坝区居民到山区做买卖和走亲访友。坝区与山区百姓间的相互了解和理解得到了加强。许多山区居民开始不再对坝区热带疾病有那么强烈的恐惧感,这当然得益于老挝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同时,坝区居民蒸蒸日上的生活与山地民族越发困难的日子形成鲜明对比,山区居民开始羡慕坝区居民的生活。山区居民发现罂粟种植时期坝区的钱财流向山区的情况一去不复返了。相反,他们自己那点微薄的收入都不断流向坝区。他们开始意识到,到坝区的甘蔗园和橡胶园里打工,或到坝区种植甘蔗、橡胶等经济作物才是他们的新出路。
2003年至2005年,帕雅洛村迎来了山区阿卡人涌入的高峰。两年间共有22户人家迁入。该村由33户一下增加到了55户。2004年2月,勐老县缅控村的7户阿卡人迁入帕雅洛村。2005年1月,勐新县阿甲迈村的9户和勐老县嘎切村的6户阿卡人搬迁入村。
2005年从阿甲迈村迁入帕雅洛的村民毕洛就告诉笔者,他之所以最终决定离开土地广阔、土壤肥沃的山区,就是因为听说在帕雅洛村种植甘蔗和橡胶一年挣的钱比在山区十年挣的钱还多,一个月打工挣的钱比山上辛劳一年挣的钱还多。仅仅几个月打工挣的钱,就使毕洛有能力开始种植自己的橡胶树了。2005年,他就种植了800株橡胶树。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他一边打工挣钱,一边种植自己的橡胶树。2006年种植了1100株,2009年种植了2000株。毕洛算过,种植这些橡胶树至少花了1.5万元人民币。2011年,他建起了一幢价值9万元的杆栏式楼房。短短6年间挣10余万元钱是早期生活在山区的毕洛不敢奢望的。
2005年底,国家允许开发的土地被55户村民抢占完毕。帕雅洛村的人地关系开始出现紧张。帕雅洛村村民也不再希望有新的山区阿卡人迁入,以免新来的人和他们争夺土地资源。尽管如此,山区阿卡人还是想尽一切办法继续迁入帕雅洛村。2012年11月,阿甲迈村的4户村民和缅控村的1户村民通过疏通帕雅洛村里威望颇高的老村长切波的关系迁入了帕雅洛村。2013年3月,又有缅控村的6户村民和嘎切村的3户村民通过各种关系迁入了帕雅洛村。
新的发展条件的逐渐成熟是山区阿卡人迁入坝区的真正动力。帕雅洛村在1987年建寨时只有7户47人,经过了漫长的15年,到2001年年底,该村才增加到25户117人。2002年该村增加了8户,达到了的33户150余人。2013年8月,该村已有75户388人。
在老挝北部的坝区及其周边地区,类似帕雅洛村这样的历经曲折过程形成的山区移民聚居村落比比皆是。这还表明,山区阿卡人并不是一直愿意生活在山区,以不光彩的罂粟种植为生,也不是有意排斥国家的移民政策,更不是要逃避国家的文明化进程,而是国家政府尚未为他们离开山区、放弃罂粟种植以及进入坝区提供新的发展机会和路径。
四、文化调适:山区“文明”融入坝区“文明”
老挝政府为移居坝区的山地民族的发展提供了通过种植橡胶、甘蔗、香蕉等经济作物获得较高的经济收益的机会和路径。这是山地民族移居坝区的根本动力,山地民族在新的家园找到了新的发展机会。他们的经济发展是迅速的,与此同时,在不断扩大的社会交往过程中,他们在文化调适方面也在不断取得进展。
同其他山区阿卡人的移民聚居村落一样,帕雅洛村的村民经常到附近的橡胶园、甘蔗园和香蕉园里打工挣钱,种植大量的橡胶和甘蔗等经济作物。2012年,帕雅洛村的土地总面积约13525亩。其中,甘蔗种植面积为255亩,占土地总面积的1.9%;橡胶种植面积达到4500亩,占总土地面积的33.3%,还有占土地总面积29.6%的轮歇地都准备种植橡胶。2012年,帕雅洛村全年的总收入约为863283元。其中,打工收入为432283元,占总收入的50.1%;甘蔗收入186000元,占总收入的21.5%;橡胶收入约10万元,占总收入的11.6%。目前,帕雅洛村里开割的橡胶树还很少,橡胶收入也较少,待到大量的橡胶树开割后,橡胶的收入将成为最为主要的经济来源。
无论是打工市场,还是橡胶种植业和甘蔗种植业,都是市场导向型的、外向型的产业,参与这些产业的阿卡人都需要同其他民族、其他地区甚至其他国家的人有更多的联系和交往。良好的信誉是一个人能够有效地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必备条件之一。人的信誉与他所属的民族群体的历史、文化、习俗以及个人自身的性格特征、人格等有关。在参与市场经济活动过程中,老挝阿卡人因民族群体的罂粟种植历史、刀耕火种方式、传统文化习俗等因素所蒙受的“污名”对他们的信誉产生了不良影响,阿卡人开始意识到消除“污名”的必要性。
阿卡人所蒙受的“污名”与他们的罂粟种植历史有直接的联系。尽管如今的阿卡人早已放弃罂粟种植,但他们曾经确实是主要的罂粟种植者之一。罂粟作为毒品原料可带来客观的经济利益,早期的殖民统治者为了殖民统治和经济利益将罂粟带入老挝,羸弱的老挝政府和各种势力则为了自身的政治、经济等利益,同殖民统治者一道扩展罂粟的种植规模,为自身的政权和势力提供资金支持。在这一过程中,阿卡人无论是被迫还是主动种植罂粟,结果都是成了为这些政权和势力贡献资金的“功臣”,但实质上他们是殖民统治者和国内各种势力压榨和剥削的对象,是受害者。当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后,老挝政府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开展了一系列禁毒工作,但在此后较长一段时间里阿卡人还是继续留在山区种植罂粟、吸毒。在全社会大力禁毒的背景下,曾经长期受殖民统治者和老挝各方势力剥削和压榨的阿卡人从受害者成为了国家乃至全世界全人类的“毒瘤”、“罪人”。一提到阿卡人,人们就认为阿卡人都以种植罂粟为生,都是“野蛮人”、“瘾君子”、“贩毒者”,他们愚昧到生病不吃药而吸大烟的地步,等等。阿卡人所蒙受的这些污名与他们的身体与性格无关,而是与民族群体所从事的罂粟种植活动和外人的成见有关,因为“污名确实是特征和成见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
既然阿卡人所蒙受的污名与罂粟种植与吸毒有直接的关系,那么,阿卡人要消除污名的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禁种罂粟和戒毒。早在2002年,帕雅洛村作为“禁毒示范村”已经全面禁种罂粟,坝子周边的其他阿卡人村寨在当年也已经禁绝了罂粟种植,即便是山区的阿卡人村寨也在随后几年逐渐禁种了罂粟。虽然罂粟已经禁种了,但阿卡人村寨里依然还有人吸食鸦片,努力戒毒成为了阿卡人消除污名的一种方式。
早在1997年,为了提高村民们的劳动素质以缓解村里劳动力缺乏带来的压力,帕雅洛村在甘蔗园老板和村长切波的带领下开展了村内戒毒工作。2002年和2004年,勐新县政府和帕雅洛村联合组织戒毒工作,帕雅洛村及附近村寨的阿卡人都到帕雅洛村的“临时戒毒所”戒毒。但这些戒毒工作都没能完全戒除吸毒者的毒瘾。此后,帕雅洛村积极配合国家的戒毒工作,把村里的吸毒者及时送到县里和省里的戒毒所。笔者在琅南塔省戒毒中心了解到:2013年8月,在省戒毒中心接受戒毒的吸毒者共计1377人,其中阿卡人有869人,占70.4%。客观上讲,阿卡人吸毒人数在减少,但阿卡人在吸毒者中所占的比重依然较高,他们需要继续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消除由此蒙受的污名。
随着禁毒工作成效的不断巩固,阿卡人虽然缓慢但也逐渐远离了罂粟种植者的形象。随着橡胶种植、甘蔗种植等项目的不断成功,“落后的”、“原始的”刀耕火种方式被放弃,但是阿卡人原有的与坝区佬族等其他民族不同的传统文化习俗依然还是民族之间相互理解的一种障碍。革除一些陋习,同时又对那些利于村寨团结以及具有积极性的传统文化的意义进行解释和宣传就成了消除外人误解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扩大化的社会交往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过程中,阿卡人开始意识到了他们的一些传统文化习俗、禁忌与现代文明的要求不相符,于是努力去修改和革除。2012年8月15日,勐新县“阿卡人文化小组”在辟遮村召开了“阿卡人文化发展讨论会”。所有阿卡人村寨的最玛、村长、文书、会计等都参加。会议达成了一些共识,形成了“勐新县阿卡人文化习俗修改方案”。具体内容如下:
(1)不再处死双胞胎,也不再忌讳有六指或兔唇的人;
(2)不再忌讳母猪在村子里生猪仔,也不忌讳母猪一胎只生一个猪仔和母狗一胎只生下一只狗仔等;
(3)不会再像过去那样把没有儿子的家庭的房屋在男主人死后拆除;
(4)不再歧视离异的女子。离异女子可以选择再嫁,也可以选择不嫁,不再嫁的离异女子死后也可以埋葬于村里的坟山上;
(5)不再忌讳已经过年的和尚未过年的村寨的村民参加彼此的葬礼。不同的阿卡人村寨过年(嘎汤帕节)的时间不统一。这样,以猪年和鼠年交替的年份为例,过了“嘎汤帕”节的村寨的人已经生活在鼠年里了,但没有过“嘎汤帕”节的人还生活在猪年里。一旦这样的两个村寨中任何一个村里死人,另一个村寨的人则不能前往奔丧,即便是亲人也不行。如今不再忌讳这点;
(6)与以前不同,如今一些非正常死亡或死在村外的人,只要举行了相应的仪式,就可以埋葬于村寨的坟山上。
老挝阿卡人的这个文化习俗修改方案参考了泰国北部阿卡人2009年制定的“阿卡人文化习俗调整方案”。老挝阿卡人根据国家法律和现实需要,并参照周边民族和其他国家阿卡人的实践,废止一些与现代文明要求不相符的禁忌和习俗,同时他们还积极地向外界展示他们的优秀文化。虽然大量山区阿卡人移居坝区使得老挝国家对阿卡人及其文化有更多的了解,并于2005年将“阿卡人”确定为49个民族之一,“阿卡”的称谓也代替过去的“戈”、“依戈”等成为唯一合法的族称。但是,阿卡人在国家层面上还是一个“新”的民族,其文化也还需要得到更多人的了解。2013年1月4日—6日在勐新县南滇宋波村举行的“首届勐新县阿卡人嘎汤帕节”就成了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展示平台。
“嘎汤帕”节在过去是阿卡人村寨各自举办的村寨性节日,2013年的“首届勐新县阿卡人嘎汤帕节”是勐新县25个阿卡人村寨联合举办的节日。这是对中国西双版纳州政府主办的哈尼族“嘎汤帕”节庆典活动的模仿。两者的程序和内容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其意义与诉求不同。老挝阿卡人举办“首届勐新县阿卡人嘎汤帕节”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向外人展示和宣传阿卡人的优秀传统文化。
节日庆典上,梅沃作为阿卡人的代表向来宾们声明“我们是祭祖的民族,不是祭鬼的民族”。他想表明的是:虽然我们不拜佛,但我们也是有信仰的民族,我们信仰的是祖先而不是鬼。以此洗刷外人心中阿卡人是祭鬼民族和“野蛮”民族的印记。并在活动现场的茅草屋里表演祭祖仪式。
接着,阿卡人在迎宾过程中展示了阿卡人从老挝主体民族佬族身上学到的迎宾礼节。在舞台上,阿卡人向来宾们展示了绚丽多彩的阿卡人民族服装,表演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歌舞。如今的阿卡人民族服装融入了一些其他民族的、流行的和时尚的元素,民族歌舞也混合了阿卡人和佬族的歌舞元素。另外,庆典上的菜肴也混合了阿卡人、佬族、周边其他民族甚至中国西双版纳地区的口味和做法。这些都表明阿卡人有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还有较强的学习运用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和文明成果的能力。
除了革除陋习和展示自身的优秀文化外,阿卡人还需要通过接受学校教育来学习那些适应新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知识。从1995年村民自愿捐款、义务出工修建学校就可以看出帕雅洛村非常重视学校教育。目前,帕雅洛村小学有3个年级(班级)63名学生,在读初中生8人、高中生5人、大学专科生1人、本科生1人,硕士研究生1人。还有1名学生到中国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学习。这些阿卡人还希望通过接受学校教育成为国家的合格公民和社会精英。
以帕雅洛村为代表的阿卡人进行的文化调适是为适应新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同时也是为适应新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进行的“去污名化”过程,其目的就是使“山地文明”融入“坝区文明”,使民族群体成为国家的合法族群,使个人成为国家的合格公民,从而维护民族群体和个人在国家和市场经济体系中的良好形象,提高民族群体和个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为民族群体和个人的发展拓展新的空间和寻找新的路径。
结 语
从勐新县帕雅洛村阿卡人的民族志这一个案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老挝北部山区阿卡人曾经拒绝实施国家的山地民族移居坝区政策,但随后国家推动的禁毒工作、“替代种植”项目以及市场经济的形成与发展等都驱使大量的山区阿卡人冲破已有的惯习主动(或许也有被迫的成分)下山,然后寻求多种发展机会,改善自身状况,洗刷污名和“野蛮”印记,融入现代“文明”,成为国家的合格公民和合法群体,提高自身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地位。山区阿卡人移居坝区以及融入“文明”的过程都是在国家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也是参与国家化进程的具体行动。阿卡人并没有像詹姆斯·C·斯科特所说的那样进行“弱者的反抗”或者运用“不被统治的艺术”来逃避国家化进程。
农民和国家的“化外民”( 或曰边缘人) 是斯科特学术关注的主要对象。阿卡人兼具了这二者的特征。斯氏有关东南亚农民的研究表明:在与试图从他们身上榨取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进行“日常”形式的斗争时,相对弱势的农民群体会拿起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日常武器进行反抗。他们还可能通过不合作、偷懒和欺骗去吞食国家的税收、耕作模式、发展政策等。 这就是所谓的运用“弱者的武器”进行的“弱者的反抗”。当面对国家化进程和“文明”进程的到来以及其传统的生计和生活方式受到威胁的时候,生活在“佐米亚” ( Zomia) 地区且游走于国家边缘的农民会运用“不被统治的艺术”来尽力逃避。 事实上,农民是一个涵括了拥有不同文化的诸多民族的概念,不同民族自身的境遇也是多样且不断变化的,不同国家的历史、性质及特征也是很不同的,很难一概而论。 老挝北部阿卡人的实际行动就强有力地挑战了斯科特的论断。当面对国家实施禁毒工作、山地民族移居坝区政策、“替代种植”等国家化进程或者“文明”进程时,居住在山区以种植罂粟为生的老挝阿卡人并没有因为他们的生产、生活、传统等受到威胁而继续游走于国家边缘、没有运用所谓的“不被统治的艺术”来逃避国家,在日常的经济生活中,老挝阿卡人也没有运用所谓的“弱者的武器”进行“弱者的反抗”。相反,在新的形势和历史条件下,阿卡人改变自身的环境( 移居坝区) ,改变生计方式( 放弃罂粟种植 橡胶),利用国家政策发展经济社会,同时利用国家提平台展示自己的优秀文化。阿卡人积极主动参与到国家化进程中,在国家化进程中进行文化调适,为融入“文明”进程和国家体系付出了努力,为适应与发展创造了新的机会。这样就有可能既让自身融为国家之一部分,又使国家的社会整合目的能够实现。
民族国家在推动民族地区或边缘地区的国家化进程中,不应该只是按照国家意 愿进行,这样可能成效甚微,就像老挝北部勐新县政府推行的山地民族移居坝区的政策招致的失败那样。正因为“国家在场对于民族文化多样性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国家应该充分的了解、尊重民族群体的文化,并为民族文化多样性发展提供机会和条件。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多样性也就 保证了民族群体得以继续发展的文化基础。同时,国家应该更多地考虑民族群体的生计问题和发展问题,并为他们提供新的发展机会和路径,正如老挝在开展禁毒工作的同时推动“替代种植”项目和相关的种植业与打工市场的形成与发展那样。国家还应该为国民融入文明进程和国家体系提供智力和制度支持。
原文正式发表于《世界民族》2014年06期
主编:何明
值班编辑:李伟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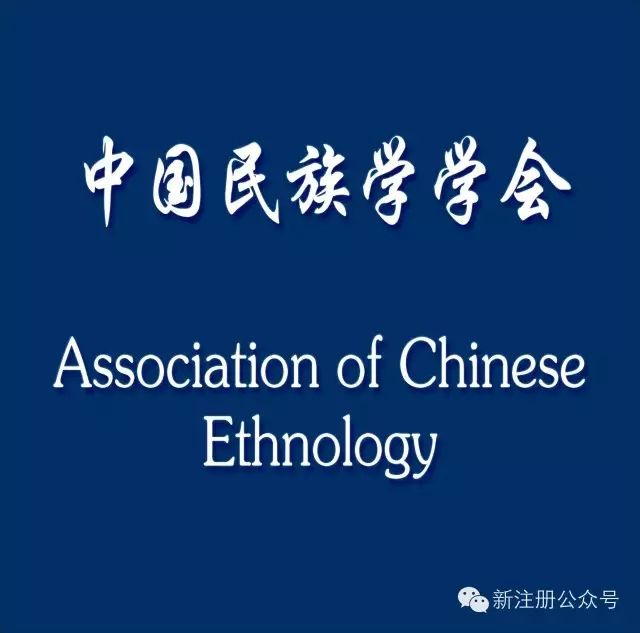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4520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4520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