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声】亲属关系是什么? ——萨林斯与蔡华的分歧

亲属关系是什么?
——萨林斯与蔡华的分歧
刘宏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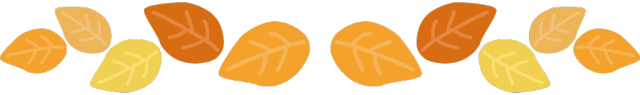
[摘要]“亲属关系是什么?”是亲属关系人类学的根基问题。它困扰过布朗、列维-斯特劳斯、施耐德等众多杰出的学者,令亲属关系人类学家在一个多世纪里坐立难安。萨林斯在83岁高龄之际又投身于这桩世纪谜题。通过对亲属关系人类学中建构论以及涂尔干和施耐德的批评,他断言亲属关系是文化的,而不是生物的,其独特性质是存在的相互性。然而,萨林斯在论述中却依然未能摆脱生物因素的束缚,而他虽声称探讨亲属关系的独特性质,实际上讨论的却是亲属关系的构成方式。事实上,早在2008年蔡华就“亲属关系是什么?”这一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解答。在解析萨林斯论述之后,本文将萨林斯与蔡华的分歧予以并置讨论。
[关键词]亲属关系;实体;存在的相互性;观念本体论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2013年,马歇尔·萨林斯的新著What Kinship Is- and Is Not(《亲属关系是什么而不是什么》[1]⑴,以下简称“本书”)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又于2014年重印。好像,“亲属关系是什么?”依然是个150年来悬而未决的谜题。
纵观本书,萨林斯认为,以往亲属关系人类学研究中的建构论阻碍了我们对亲属关系的认识,而亲属关系研究的路标性人物施耐德(David Schneider)又将亲属关系引向贫瘠的领地,相比之下,涂尔干虽然未能界定血亲关系是什么,但萨林斯却认为涂尔干隐约摸到了血亲关系的实质。为此,萨林斯首先批评了其所谓的亲属关系研究中的建构论,进而在批判了施耐德和涂尔干之后导引出亲属关系的独特性质即存在的相互性(mutuality of being),并从多方面展开论述。
在批评既往研究和阐释自己观点时,萨林斯使用了大量的民族志材料。他很坦诚地说,其使用诸多民族志材料展开论述的目的,并不是要经验地证明而仅是例示他的观点[1](p.2) ⑵。由此,在展示萨林斯论述的同时,笔者也将简要陈述他所列举的案例,并探讨这些案例是否足以“例示”他意欲表达的观点。
整体而言,尽管萨林斯颇有洞见,不过他在批判其所谓的建构论时亦犯下了他力图避免的错误;他虽明确提出要论述亲属关系的独特性质是存在的相互性,但他在论述中却又避开了其力图追求的目标。据此,本文将在介绍萨林斯对建构论的批评和其所谓的存在的相互性时,也对萨林斯论述中的失误与不足予以商榷,最后再结合蔡华的研究结果重新探讨亲属关系的性质问题。笔者的论述将紧紧围绕“亲属关系是什么?”这一问题来展开,而不讨论“亲属关系与其他因素的关系”。
一、萨林斯对建构论的批评与萨林斯的失误
萨林斯总结了当前亲属关系研究中的建构论,并将其概括为:“通过生殖(procreation)、生物性亲子关系(filiation)或继嗣(descent)⑷ 建立的任何关系也都可以借助适当的文化行动而后天地或行为展演地建立。”[1](p.2) 尽管萨林斯未在本书中对此“建构论”给予明确的解析,但通过对本书论述的分析,笔者发现,萨林斯将其概括的建构论分解为三个子命题。其一,血亲关系可由生殖、生物性亲子关系或继嗣来建立;其二,血亲关系亦可由后天的社会文化行动来建立;其三,前者所建立的血亲关系是基础,而后者则借助行动在实践中模拟前者。
针对建构论的上述命题,萨林斯认为,它们是时下亲属关系人类学研究的教条,并从三个方面对其予以批评。其一,生与被生的联系并不必然导致血亲关系(kinship)的产生[1](p.5);其二,由繁殖所建立的血亲关系与后天创建的血亲关系之间甚至未必存在什么本质差别[1](p.5);其三,社会建构的血亲关系是基于性繁衍而成的血亲关系的必要补充,性繁衍和社会建构共同在时间中塑造亲子之间的联系[1](p.8)。在本文中,萨林斯对建构论的批评将被逐一展开,同时,萨林斯在批评建构论时的失误也将被予以讨论。
在批评建构论的第一条命题时,萨林斯认为,考虑到人类社会文化的多样性,连结一个人和他/她生物后代的是各种被传递的实物,比如血液、精液或骨头等等,而实物如同“密码”,在生殖过程中它不只是作为物理的实物被传递,也作为社会地位被传递[1](p.4)5⑸这说明,生殖过程有生物的一面,但同时又有社会的一面,而并非建构论第一条命题所说仅仅是生物的。但是,令人疑惑的是,萨林斯又佐引努德尔(Nuttal)的研究来说明血亲关系与生殖无关:在格陵兰岛的因纽特人(Greenland Inuit)中,如果一个孩童被冠以其母亲的父亲的名字,那么他将称他的生母为“女儿”,称他生母的丈夫为“女儿的丈夫”,称他母亲的母亲为“妻子”。[1](p.5),[2](p.276)⑹在本案例中,“女儿”、“妻子”等看似是亲属称谓,实乃是对人的分类,它的改变的确与生殖无关,但它也并不造成血亲关系的改变。⑺来自中国闽南的学生曾告诉笔者,闽南地区也存在亲生母女以姐妹相称的事实。然而,难道说母女以姐妹相称后,父女之间的血亲关系会发生改变?其实,已有研究发现,即便是亲属称谓也并不与血亲关系体现一致的规则,亲属称谓并不是判定血亲关系的依据。[3] 由萨林斯所举的这个案例来看,他对血亲关系与亲属称谓的认识依然停留在亲属关系人类学的初创时期,即摩尔根式的以亲属称谓来探讨血亲关系。在此,我们看到,尽管萨林斯以多样的民族志案例来批评建构论的第一条命题,但他却忽视了亲属关系人类学已有的重要结论,以至于出现其所引材料不支持其论断、甚至与其整体结论相冲突的情况。
在批评建构论的第二条命题时,萨林斯在人类学民族志中发现了一个极具特点的案例:在新几内亚人中,无论是生物繁衍还是社会实践造成的血亲关系都经由“脂肪”的传递而实现。当地语言中的kopong被翻译为英文grease或fat。“最初源于土地”的“脂肪”被当地人视为活物的基本物质。父亲的精液和母亲的乳汁将“脂肪”传递到孩子体内,进而建立了一个孩子和他生身父母的重要联系。同时,甜薯和猪肉中也含有“脂肪”,这样,共享食物或共享产自同一块土地的食物也具有相同的效果。这样,移民者的子辈或孙辈将被完全整合为当地的亲属,两兄弟的后代也因共享土地而成为类似的亲属。[1](p.5-6) 由此,萨林斯认为,在由繁殖所建立的血亲关系与后天创建的血亲关系之间甚至未必存在什么本质差别。[1](p.5) 这便是说,建构论第二条命题便毫无意义了。因为建构论要试图在由生殖所建立的血亲关系与由社会文化行动所建立血亲关系之间做出区分,但新几内亚人的案例却表明它们本就是一体。但是,笔者发现,事实上,新几内亚人所谓的“脂肪”明显不是生物学所界定的某种高分子链团,而是当地人关于生殖的地方性知识,其本身就是社会的和文化的,而不是生物的。新几内亚人的案例中并不包含什么生物繁衍,该案例所表达的是新几内亚人和新卡里多尼亚人独特的繁殖观念及作为其社会文化后果的血亲联系。可见,在新几内亚人的亲属关系中,不是生物繁衍所建立的血亲关系与后天行动所建立的血亲关系没有本质差别,而是由当地特殊的繁殖观念所规定的血亲关系与后天行动所建立的血亲关系没有本质差别。在此,萨林斯在瓦解建构论的第二条命题时,又将生物因素埋藏到血亲关系之中,而他的整体观点又是:亲属关系不是生物的,是文化的。[4](p.155)⑻
在批评建构论的第三条命题时,萨林斯援引泰勒(Anne-Christine Taylor)的研究:亚马逊的西瓦罗人(Jivaro)父子关系便是基于性繁衍和社会建构而共同实现的。西瓦罗人“并不认为生殖可以确保父母与其孩子的重要联系。”[1](p.8) 血亲关系的建构形式呈现出大量的可能性。[1](p.8-9) 这便是说性繁衍在血亲关系的建立中不具有独立地位,更不可能成为血亲关系建构的基础。
至此,萨林斯完成了对建构论的最后批评。然而,我们看到,在批判建构论的最后一个命题时,萨林斯依然未能摆脱生物学的影响。尽管在本书中他明确声称形成血亲关系的后天方式有多种(共同居住、分享食物、轮回转世、共同记忆、一同劳作、血缘兄弟、共同的遭遇、收养和友谊等),[1](p.9) 亲属关系与生物无关,并用大量篇幅来讨论这个问题[1](p.62-86)。但是,在具体的论述中,他又是一位明显的生物学论者。如果是性繁衍和社会建构共同在时间中塑造了亲子联系,那么生物因素已经籍由性繁衍而植入到了亲子关系乃至血亲关系之中。可见,尽管萨林斯尖锐地批判了建构论的缺陷,但他却从未将生物因素从血亲关系中剔除。[5](p.295)
尽管如此,萨林斯依然认为,由于施耐德对西方人执着于以生物学来理解其他社会的血亲关系进行了批评,也由此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建构论,但建构论依然未能摈弃生物因素。[1](p.11) 在血亲关系研究中,萨林斯可能认为,只有涂尔干和施耐德曾力图摆脱生物学的困扰,因为他在本书中只单独批评了这两位学者。
萨林斯认为,施耐德在摈弃生物学因素的同时,却又在文化上否认血亲关系的存在,即在世界范围的事实层面上,并不存在一种事实可以在文化上被称为血亲关系。[6] 萨林斯认为,由于施耐德在社会科学自视甚高的帕森斯年代接受学术训练,而那时,社会结构和文化秩序被彻底地区分,这样,施耐德批评既往血亲关系研究时的立场便已确定:由社会行动和社会关系所组成“规范系统”与由“符号和意义”所构成的“文化系统”之间具有先验的彻底区分[1](p.12-13)。萨林斯认为,施耐德所界定的“文化”具有本体论的特征,而施耐德又只在这个范围里寻找血亲关系[1](p.13)。这样,由于民族和宗教也因其符号特征而被涵盖在“文化系统”里,如此便无法在文化的意义上将血亲关系与民族、宗教区别开来。[1](p.14) 萨林斯认为,由于施耐德将文化与社会的区分视为本体论的区分,因而忽视了社会关系的符号建构。如此一来,施耐德便只能无奈地宣称“在纯文化层面上,不存在血亲关系之类的东西”。[1](p.16) 在萨林斯看来,施耐德的结论宿命地体现了帕森斯学派的痼疾,而因循同一学派传统的格尔兹·克利福德也犯了同样的错误。[1](p.16)
另外,涂尔干虽对亲属关系的非生物属性言之凿凿,不过,在萨林斯看来,涂尔干将血亲关系从血缘和生物系谱中明确地区分出来,这仅仅是涂尔干中心命题的推论,即社会事实不是自然现象,作为社会事实的血亲关系不能还原到生物学或心理学。[1](p.17) 尽管如此,萨林斯认为涂尔干猜到了血亲关系的重要特点:存在的相互联系(mutual relations of being)、在彼此的实存中互渗(participation in one another’s existence)。[1](p.18) 萨林斯关于“亲属关系是什么?”的见解也可由涂尔干的这两个短语来概括。
二、萨林斯的提案:存在的相互性
在本书论述之初,萨林斯便写道:“kinship”具体性质是“存在的相互性”(mutuality of being),即“亲属是这样一群人,他们相互内在地渗入到对方的存在中,他们是彼此的成员。” [1](p.ix) 亲属制度(kinship system)是主体间互渗的复合体(a manifold of intersubjective participations),也即存在的相互性构成的网络。[1](p.20)
对此,萨林斯十分警觉地意识到,他从哲学中拾起的两个概念可能会带来认识上的混乱和模糊。以 “存在(being)”来讨论亲属关系(kinship)可能会坠入黑暗的哲学深潭,而过时的概念“互渗(participation)”更会带来认识上的混乱。[1](p.32) 因为存在亦包含着实存(substance)乃至物质(materiality)的意思,同时,在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中,存在又绝不是物质性实存(material substance),这使得存在的相互性与亲属关系的关系显得模糊。[1](p.32) 相比之下,列维-布留尔提出的“互渗”概念包含着共享的存在(shared existence)的意思,这个概念否认了哲学中关于“一”与“多”、自我与他者的对立。“互渗”使得事物具有了共同存在性或成为二元整体。[1](p.33) 结合这两个概念可以看到,互渗不是存在者(beings)的融合,而是存在(existence)的条件。[1](p.33-34) 在萨林斯看来,列维-布留尔的“互渗”概括了亲属关系中诸如共同的继嗣、世系、氏族之类群体的特征[1](p.34)。因此,尽管可能会出现混乱和模糊,萨林斯还是使用了“存在”和“互渗”这两个分析性概念。
以上述认识为背景,为了阐明亲属关系的特性即存在的相互性,萨林斯征引了庞杂的民族志事实和其他学者的诸多论述。整体来看,萨林斯试图从以下四个方面来例示亲属关系的特性:“非个体的人”(dividual person)、“我式血亲关系”(kinship I)、彼此的相属以及跨物种的血亲关系。这四个方面将在下文中一一展开,同时萨林斯论述的不足之处亦将被讨论。

(一)非个体的人与存在的相互性
“非个体的人”(dividual person)本由马里奥特(McKim Marriott)和斯特拉森(Marilyn Strathern)分别在他们1976和1988年的著述中提出,萨林斯只是借此术语来统领众多民族志材料以展开对亲属关系之存在相互性的探讨。[1](p.19) 斯特拉森在研究美拉尼西亚人时发现: “美拉尼西亚人认为人既是各自单独地被孕育构造的,也是非个体的。人包含了普遍的社会性。的确,人是由各种关系造就的多元综合体。单个的人被想象为社会的微缩。”[1](p.24)萨林斯发现,人被斯特拉森描述为多元他者之行动和实物(substances)的单一聚合体(composite site),而这种人观也出现在汤加人、特洛布里安德人、波利尼西亚、中国的明朝和古埃及的某个时期中。萨林斯认为,非个体(dividual)可能是前现代主体性的普遍形式。[1](p.25)
为说明“非个体的人”的普遍性,萨林斯征引了几个很有价值的民族志案例。其一,在新卡里多尼亚(New Caledonian)社会,当一位老人被传教士林哈德(Maurice Leenhardt)告知:基督教为当地引入了灵魂(spirit/esprit)观念。那老人当即否认说:“你没有带给我们灵魂,我们早就知道灵魂的存在,你带给我们的是身体。”[1](p.19) 对此,萨林斯征引巴士底(Bastide)的评论:美拉尼西亚人仅仅将自身构想为互渗的节点,相比于他们内在于自身,他们更外在于自身。也就是说,人在本质上处于其世系和图腾之中。与此不同,传教士则使得他们以自己的身体为界将自身从世系和图腾中区分出来。巴士底认为新卡里多尼亚人也是非个体的(divisible),而非单独的(not distinct),因为自我的许多方面广泛分布在他人的自我之中,构成一个人的多种因素也渗入到了他人的实在(realities)之中。[1](p.19) 笔者认为,萨林斯所举的这个例子的确在展示“非个体的人”。其二,在德昌布利人(Tchambuli)社会,众多图腾名称为氏族成员所共有,这些名字涵盖了祖先们的名字以及祖先们拥有及赖以维生的领土和资源。只有继承父母双方亲属的名字,氏族成员才能与父母双方亲属建立亲密关系。这样,要成为一个人就要嵌入这种关系。[1](p.26) 由此,萨林斯认为,不仅人是关系的具象化,而且共享名字又使人成为存在的综合体。[1](p.26) 对此,笔者认为,依据民族志常识,一个人继承父母双方亲属的名字,这仅仅是其社会身份得到认可的外在标识,而并非名字本身决定了他与其父母的关系。继承名字的实质是获取身份,而身份又将当事人与其他具有相同身份的人整合为一个整体。所以,这种非个体性是身份的特点,而不是人的特点。在此,萨林斯又列举了一个与其论述相违的案例。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非个体的人”是一种人观,而人观并不等于亲属关系。萨林斯警觉到了这一点,他说他讨论“非个体的人”并非从人观角度来看,而是关注自我在众多他者中的人际间分布,就像众多他者合并成一个主体,因为,这里所讨论不是人的性质,而是各种关系的特征(笔者加粗)。[1](p.25) 萨林斯认为,斯特拉森未能处理“非个体的人”与构成这些人的隐性关系,而恰是主体间的关系构成了亲属次序的基本要素。在人类学的意义上,非个体(dividual)不仅是对个体(individual)的否定,它更包含了亲属关系(kinship relations)的互渗含义。[1](p.26) 萨林斯还举例说,由于夫妻是一个“二元体”,夫妻之间会相互影响,这样,丈夫在社区之外从事重要事务时,留在社区内的妻子便需要遵守许多行为禁忌。[1](p.48) 同样,基于存在的相互性,原罪(sins)由父向子女乃至向其他亲属传递。[1](p.49) 类似地,在复仇时,只要杀死杀人者所属群体的任何一个成员即可。萨林斯认为,这都表明:离散的不同主体共享同一个实体。[1](p.21,50)
然而,在笔者看来,尽管亲属关系可能体现出“离散的不同主体共享同一个实体”,但它只是“前现代主体性的普遍形式”(笔者加粗),而不是亲属关系的独特特征。另外,如果说作为不同“主体”的亲属们,他们共享着同一“实体”,那么这个被共享的“实体”又是什么?这才是根本的问题,萨林斯却弃之不顾。他一面声称要“例示”亲属关系的独特性质,一面又在遇到亲属关系实体之时却避而远之。

(二)我式血亲关系与存在的相互性
萨林斯借用约翰森(Johansen)提出的“我式血亲关系”(kinship I)[1](p.35),试图分别从人称代词、物主代词、亲属称谓和共享某物等方面来探讨“我式亲属关系”中所蕴含的存在的相互性。
人称代词“我(I)”被毛利人用来指称说话者的整个血亲群体,包括死去的先人和在世的亲人。毛利的部落不仅由他们的祖先来确定自身的身份,他们的行为特征也被祖先所刻画。有时,毛利人用同一个人称代词“我”在同一个故事中指称自己和自己英雄的祖先。[1](p.34-35) 在波利尼西亚和美拉尼西亚,拉姆齐(Rumsey)发现,在同一个对话中,由于参考系的转换,人称代词“我”可以分别指称说话者、说话者所属的亲属群体或早已去世的具有英雄事迹的酋长。[1](p.27) 萨林斯借此来说明人称代词所蕴含的存在的相互性,但我们不禁要问,这难道是说话者与其英雄祖先合二为一了吗?对此,萨林斯很警觉地说,当然,人称代词所指称的多个“我”并不必然与说话者本人的社会实践相一致。[1](p.27) 由此,笔者断言,人称代词“我”可能暗含了说话者与其所属亲属群体及英雄祖先的某种同一性,但由于说话者本人的社会实践并未因此而改变,那么,人称代词“我”只是说话者的修辞,而非事实。这样,如果在说话者与其祖先之间具有存在的相互性,那也仅仅是语言修辞上的,而非事实上的。
此外,在从亲属称谓探讨“我式亲属关系”时,萨林斯引用威尔逊(Wilson)等人的看法,即亲属称谓暗含了相连的存在的种类和/或程度。比如,马达加斯加的卡热博拉人(Karembola)认为兄弟和姐妹是“一个人”,他们“彼此拥有”。[1](p.23) 另外,卡洛威人(Korowai)亲属称谓的物主人称前缀是在强调被称谓者是称谓者的谓词,称谓者把被称谓者视为一个包括于自身存在之内的客体。[1](p.23) 这令笔者联想到两个汉语词汇——“兄弟”与“手足”。按照萨林斯的逻辑,汉人的兄弟被称为“手足”,手足又是人身体的一部分,那么,兄弟关系是一种内在关系。但显而易见,这仅是表象,其根基为汉人对个体血亲身份同一性的认识。[7][8]
由此,可以说,萨林斯试图通过代词和称谓来观测亲属关系,便只能看到其所再现的亲属之间的关系,但却遗漏了该关系得以产生的原因。我们看到,他所能论述的,也仅仅是语义分析,至于“在社会生活中,兄弟姐妹如何是‘一个人’?”、“他们之间为何会有这种关系而非亲属之间却没有这种关系?”等之类的问题,萨林斯也避之未答。

(三)彼此相属、跨物种的亲属关系与存在的相互性
萨林斯还从“彼此相属”来探讨存在的相互性,为此,萨林斯列举了丰富的案例。关于后天的血亲关系(postnatal kinship),楚克人(Trukese)认为“源自同一条独木舟的即为同胞”,这是在说,那些在危机四伏的大海上彼此支持的人们就是同胞。[1](p.29) 格陵兰岛的因纽特人也有类似的情况。[1](p.30) 这种彼此的相属也可能并不需要外在的标识。英国Alltown人的“家族亦视自身为彼此相互所属的人们”。[1](p.22) 类似地,东非大裂谷的尼亚库萨人(Nyakyusa)也认为血亲们是“彼此的成员”,他们将生物血缘亲属(consanguines)和姻缘亲属(affines)都视为相互存在(mutual being)的亲属关系(kinship)[1](p.22)。与其相似,特纳(Victor Turner)认为,由于母系联系而居住在一起的恩丹布人,其母系血亲渗入到彼此的实存(existence)中。[1](p.22) 卡斯滕(Janet Carsten)在研究收养者时也获得了相似的结论。那些寻找其生身亲属(birth kin)的被收养者,他们对其生身父母一无所知,在卡斯滕看来,他们明显经历着一种自我的“破碎与残缺”[1](p.22)。据此,萨林斯认为,在这种人观中,血亲关系不仅仅是独立个体之间的关系;在这种人观中,“亲属们内在于自我之中”。[1](p.22) 再一次地,我们看到,萨林斯在从彼此相属的角度讨论亲属关系时,他仅仅关注于当地人彼此相属的方式及当地人的话语中所暗含的存在的相互性。很明显,他似乎并不着意于讨论亲属关系的内容和性质,而仅仅关注亲属之间的关系。如果不在亲属关系与非亲属关系的差别中刻画“亲属关系”的特征,那么我们便不可能知道亲属关系的边界和性质。
在萨林斯看来,存在的相互性也包含在跨物种的亲属关系(trans-specific relations of kinship)之中。比如,亚马逊妇女种植的植物就是她的孩子,亚马逊男人猎获的动物就是他的姻亲。萨林斯认为,这不是隐喻,而是一种关于伦理、仪式和实践行为的社会学。于毛利人而言,血亲关系是宇宙论的,因为包括动植物在内的所有东西都发源于相同的天父和地母。毛利人进入森林狩猎,就像是串亲戚。[1](p.30 )在毛利人中,苍蝇、鲸鱼、鸟类、树木、库克船长和将一个部落运往新西兰的独木舟,所有这些存在物都与毛利人共享相同的继嗣、血亲关系和人观等本质属性。[1](p.31) 在此,萨林斯将亲属关系扩展到了宇宙论的层面。但是,很明显,跨物种的亲属关系与人类内部的亲属关系这两者的性质完全不同。人类之间的亲属关系不仅包含血亲关系,还包含亲属称谓、居住制度、分家析产等。相比之下,跨物种的亲属关系只具有“亲属关系”这一修辞的、隐喻的名号。跨物种的亲属关系如果存在的话,它也将是另外一个主题。
三、余论:亲属关系是什么?
整体而言,萨林斯认为,存在的相互性足以描述亲属关系的多样构成方式,无论构成方式是先天/后天,是基于纯粹的“生物学”还是纯粹的行为展演,或它们两者的某种结合。由于共享某种物质不是构成血亲关系(kinship)的普遍条件或基本条件,最好将共享某种物质理解为共同存在(common being)的文化假设。[1](p.28) 基于此,萨林斯冒险推测:构成亲属关系(kinship)的所有方式在本质上是一样的[1](p.29), 即其本质皆为存在的相互性。萨林斯认为,存在的相互性具有三重效果。其一,存在的相互性涵盖了民族志中各地血亲关系构成的多样性,无论血亲关系是由繁殖、社会建构或这两者的某种综合所构成,存在的相互性皆可涵盖它们;其二,它同样能够应用到个人间的亲属联系,无论是血缘的、姻缘的,还是继嗣的群体安排;其三,存在的相互性将逻辑地激发亲属间的神秘效果,即一个人的作为或经历使其亲属具有相同的经历。就像圣经中的原罪在父子间传递。[1](p.2) 然而,由于亲属之间既团结又冲突,因而“存在的相互性”必然需要解释为什么亲属之间存在冲突。萨林斯认为,亲属间的存在的相互性因空间和生物谱系的渐远而成比例地缩减。[1](p.53)
至此,我们看到,萨林斯真正关注的并非其书名所指出的。其一,他声称亲属关系不是生物的。[1](p.62-89) 但是,他又认为存在的相互性可以解释由繁殖所构成的亲属关系。这便是说,萨林斯依然认为亲属关系具有生物性,只不过这种生物性是可以被存在的相互性所解释。这样,他不仅未撇清亲属关系与生物关系的区别,反而隐含地承认亲属关系的生物性。不仅如此,他还认为亲属之间的“存在的相互性”会因生物谱系的距离而缩减。这样,他更是将存在的相互性立足于生物血缘之上,而且也没有阐明为何作为一种性质的“存在的相互性”会因生物血缘关系的远近而存在程度的差别。
其二,萨林斯也并未关心“亲属关系是什么而不是什么”,他关注的是“亲属关系的构成方式是什么”。萨林斯试图要说明的命题是:亲属关系的独特性质(specific quality)是存在的相互性。[1](p.ix) 然而,在具体的论述中,他转而讨论亲属关系之构成方式的性质。很明显,这两个问题处于不同的层次,前者居于基础位置,而后者是次生的。萨林斯在论述中混淆了这两个问题。尽管他以庞杂丰厚的案例在“非个体性”、“我式亲属关系”、“彼此相属”等方面展开铺陈,进而说明离散的主体如何共享同一个实体,并以心理学的相关研究来加以佐证。但是,他却并未考察这个实体,而仅仅是以“存在的相互性”替换了“离散的主体共享同一个实体”这一表述。虽然他提出了“存在的相互性”这一术语,却只是回顾了哲学上关于“存在”的讨论,而并未言明他所说的存在究竟指的是什么。亲属关系是什么这一问题并未得到解答。整体来看,讨论亲属关系时,萨林斯仅仅考虑亲属之间的关系所具有的特点,即其所谓的存在的相互性,但他却从未讨论亲属之间的关系建立在哪两类或多类因素之间,也未讨论作为整体的“亲属关系”为何因社会文化而有差异。在他抽象地谈论关系的特征时,却未能推进我们对亲属关系独特之处的理解。
其三,萨林斯试图讨论亲属关系的独特性质是存在的相互性,但又在论述的末了提出,存在的相互性还体现在礼物交换和巫术魔法中;[1](p.58-60)
其四,萨林斯在论述中的相互冲突与他对“kinship”的认识和使用上的前后不一相对应。他只看到作为一种关系的“kinship”和作为一个群体构成方式的“kinship”,但却未对作为一种关系的“kinship”所包含的血亲关系和姻亲关系做出性质上的区分,而在探讨作为一种构成方式的“kinship”时又将其所谓的“存在的相互性”拓展到“kinship”之外[9](p.281,283)⑿。
总体来说,萨林斯既混淆了亲属关系与血亲关系,又执意使用两个模糊的分析性概念——“存在”与“互渗”,这导致他既未能回答其声称要回答的问题,又在论述中出现许多相互矛盾之处。
萨林斯关于亲属关系的讨论最早发表于2011年,然而,早在2008年,在亲属关系领域持续工作近20年中国学者蔡华已经就这个问题作了回答。[10] 萨林斯在界定了建构论的研究取向之时,也对建构论的生物学立场加以批评,殊不知,对亲属关系研究中生物学立场的批评早在2008年已经完成;[3](p.35-77) 萨林斯曾将“亲属关系是文化”作为一个重要标题来引领其论述,殊不知,早在2008年,亲属关系的文化性质这一结论已经被获得。[3](p.87) 萨林斯在“存在”这一层面上讨论亲属关系构成方式的性质,而蔡华却是在“存在”这一层面上讨论亲属关系的性质。
关于亲属关系的内容和性质的讨论,蔡华的经验证明起始于在逻辑上可能又事实上在人类社会出现的四类身份认定制度,即父系制、母系制、不对称双系制和对称双系制。每一种制度又都建立于特定的身体再现系统,即当事群体坚信的关于个体身体来源的观念。虽然每一种身体再现系统都是对自然事实生育的再现,但由于身体再现系统是集体认可的文化观念,它便是文化事实,而非生物事实。[3](p.24-34) 由此,文化事实成为各种亲属制度等社会事实的决定因素。[3] 以汉族为例,父子关系具有“父子同气”的特征,我们看到,父子关系这一社会文化事实具有“气”这一本体论含义。其实,此类文化事实皆具有本体论的含义。这便是蔡华所提出的“观念本体论”[3](p.119-120) 的一个例子,它为解释人类社会亲属制度的多样性与统一性提供了基础。
具体地,在亲属关系中,占据本体位置的是对身体再现系统为真的信念。[3](p.24-34) 由此,汉人社会的身体再现系统确定了父子之间“天然的”不可断绝的文化血脉联系,而纳人的身体再现系统则仅仅确定了母子女之间“天然的”不可断绝的文化血脉联系。正是这种具有本体含义信仰造就了血亲成员之间的社会联系,汉人社会的父子之间以及纳人社会的母女之间具有了相互内在于自身的含义,即具有了存在的相互性。
可见,尽管萨林斯敏锐地抓住了亲属之间的存在的相互性,但由于他并未廓清存在的相互性在亲属关系领域里的根基,这使得存在的相互性失去了具体的内容,而只有抽象的“相互内在”。然而,在蔡华廓清亲属关系的根基与特质是文化血亲观念之时,亲属关系不仅与生物关系划清了界线,同时,亲属关系本身的独特性质亦被发现。
总之,布朗从继嗣关系出发、列维-斯特劳斯从联姻出发[11]、施耐德从纯文化的角度出发,皆未能揭示亲属关系的性质和一般特征。萨林斯在本书中所做的工作却只是一个不完全的文献综述,他所提出的“存在的相互性”也曾被不同学者以不同方式表达过。尽管他意欲揭开亲属关系的底牌,但却不晓得底牌已经被揭开。若早知晓这些,或许他便不会徒劳地揭开他摸到的倒数第二张牌,也不会认为它是底牌。虽然萨林斯未能说明亲属关系的独特性质,并转而探讨亲属关系的构成方式以及这种构成方式与礼物和巫术的相似性,但正是在这一点上,萨林斯拓展了我们的认识。只是,萨林斯以弗雷泽式的散漫比较、对民族志材料的旁征博引、以例示而非论证的方式展开陈述,这使得其论述的命题与洞见几乎淹没在了庞杂的材料中。
注释:
*澜清、张帆和富晓星作为本文初稿的首批读者,提出了颇为有益的建设性意见,在此致谢。
⑴本书主要内容最初以“What Kinship Is”为题于2011年分两期连载于英国皇家人类学会会刊,后经增补和修改,最终成书,并于2013年首次印刷出版,2014年重新印刷。书名较为准确的中译应为《亲属关系是什么而不是什么》,而不是《血亲关系是什么而不是什么》。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kinship”是本书的核心概念,其英文意思为“血亲关系”,但它在书中多次出现时的意思并不一致。在本书中,“kinship”有时仅指父或母与子女的关系、有时则指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有时也指血亲关系、有时又将血亲关系和姻亲关系统统包含,这个词还被用来指称亲属群体。因而,根据全书的内容,书名中的“kinship”译为亲属关系更为恰当。尽管如此,笔者不得不说,由于在本书中“kinship”时而是指某种关系,时而指代某类群体,而在指代特定关系时又有不同的具体含义,这不仅使该著的论述不再通畅,也给读者造成理解上的困扰。这是萨林斯在写作与概念使用上的失误,为此,笔者在评述时将根据具体的语境以相应的中文来替代该词。
⑵由于萨林斯所举案例来源于众多的民族志,而笔者未能查看萨林斯所有征引文献的原文予以核对,此为本文的缺憾。
⑶众多学者在研究亲属关系时,更多地关注亲属关系与空间、地方、政治、经济和宗教的关系,而对亲属关系是什么却未加审查。 在讨论亲属关系与其他因素的关系时,众多学者几乎仅仅是将亲属关系视为一种社会关系网络,而未考虑这个社会关系网络的性质与其他社会关系网络的性质究竟有何差异。
⑷“filiation”和“descent”这两个术语,一个是法语词汇,另一个是英语词汇,它们所表达的意思基本相同,但亲属关系研究者在使用此一术语时却在表达着不同甚至相互排斥的含义,具体可参见蔡华《人思之人: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统一性》一书的第85到87页。纵观萨林斯的论述,这两个词指的是生物血缘关系的延续,而不涉及权利义务关系。在萨林斯的论述中,这两个词与“procreation”皆指生与被生的联系,即生物性的联系。
⑸萨林斯的此一论断援引于施耐德,该论断的确能够指出建构论的盲点,然而,萨林斯却将生物因素视为了血亲关系的一部分。这与其重要结论“亲属关系不是生物的,是文化的”相冲突。
⑹对此,施赖奥克(Andrew Shryock)认为萨林斯的论述中存在矛盾:萨林斯试图通过生物性系谱称谓(genealogical term)来展开论述,而萨林斯要论述的恰是亲属关系不是生物的。
⑺来自与蔡华教授的私人交流。
⑻对此,罗伯特·金(Robert King)认为,虽然萨林斯强烈表达了亲属关系是文化的,但他却从未说明文化从何而来,就好像文化“就那样生成了”(just growed)。这是萨林斯需要面对但却回避另一个重要问题,即不说明文化是什么、文化从何而来,那么说“亲属关系是文化”,这便毫无意义。
⑼罗伯特·帕金(Robert Parkin)对萨林斯的论述亦有类似的评价。
⑽尽管萨林斯基本赞成斯特拉森的结论,但他与拉姆齐(Alan Rumsey)私人交流时,他们一致认为斯特拉森的看法存在无法解释的困境,即美拉尼西亚人既是个体又是非个体。萨林斯认为,斯特拉森的意思很可能是:非个体的人(a dividual person)是单独的实体(an individual entity)。
⑾比如,若未能将“渗入到彼此实存”中却因战乱离散的恋人所经历的“破碎与残缺”与亲属之间的存在相互性进行区分,那么,作为亲属关系之独特性质的存在的相互性就不可能成立。
⑿在王斯福看来,萨林斯所说的存在的相互性亦在友谊和个人间的信任中出现。这便是说,存在的相互性本身并非亲属关系的特点,而亲属关系区别于其他关系之处并未被萨林斯说明。
注释:
*澜清、张帆和富晓星作为本文初稿的首批读者,提出了颇为有益的建设性意见,在此致谢。
(1)本书主要内容最初以“What Kinship Is”为题于2011年分两期连载于英国皇家人类学会会刊,后经增补和修改,最终成书,并于2013年首次印刷出版,2014年重新印刷。书名较为准确的中译应为《亲属关系是什么而不是什么》,而不是《血亲关系是什么而不是什么》。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kinship”是本书的核心概念,其英文意思为“血亲关系”,但它在书中多次出现时的意思并不一致。在本书中,“kinship”有时仅指父或母与子女的关系、有时则指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有时也指血亲关系、有时又将血亲关系和姻亲关系统统包含,这个词还被用来指称亲属群体。因而,根据全书的内容,书名中的“kinship”译为亲属关系更为恰当。尽管如此,笔者不得不说,由于在本书中“kinship”时而是指某种关系,时而指代某类群体,而在指代特定关系时又有不同的具体含义,这不仅使该著的论述不再通畅,也给读者造成理解上的困扰。这是萨林斯在写作与概念使用上的失误,为此,笔者在评述时将根据具体的语境以相应的中文来替代该词。
(2)由于萨林斯所举案例来源于众多的民族志,而笔者未能查看萨林斯所有征引文献的原文予以核对,此为本文的缺憾。
(3)众多学者在研究亲属关系时,更多地关注亲属关系与空间、地方、政治、经济和宗教的关系,而对亲属关系是什么却未加审查。 在讨论亲属关系与其他因素的关系时,众多学者几乎仅仅是将亲属关系视为一种社会关系网络,而未考虑这个社会关系网络的性质与其他社会关系网络的性质究竟有何差异。
(4)“filiation”和“descent”这两个术语,一个是法语词汇,另一个是英语词汇,它们所表达的意思基本相同,但亲属关系研究者在使用此一术语时却在表达着不同甚至相互排斥的含义,具体可参见蔡华《人思之人: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统一性》一书的第85到87页。纵观萨林斯的论述,这两个词指的是生物血缘关系的延续,而不涉及权利义务关系。在萨林斯的论述中,这两个词与“procreation”皆指生与被生的联系,即生物性的联系。
(5)萨林斯的此一论断援引于施耐德,该论断的确能够指出建构论的盲点,然而,萨林斯却将生物因素视为了血亲关系的一部分。这与其重要结论“亲属关系不是生物的,是文化的”相冲突。
(6)对此,施赖奥克(Andrew Shryock)认为萨林斯的论述中存在矛盾:萨林斯试图通过生物性系谱称谓(genealogical term)来展开论述,而萨林斯要论述的恰是亲属关系不是生物的。
(7)来自与蔡华教授的私人交流。
(8)对此,罗伯特·金(Robert King)认为,虽然萨林斯强烈表达了亲属关系是文化的,但他却从未说明文化从何而来,就好像文化“就那样生成了”(just growed)。这是萨林斯需要面对但却回避另一个重要问题,即不说明文化是什么、文化从何而来,那么说“亲属关系是文化”,这便毫无意义。
(9)罗伯特·帕金(Robert Parkin)对萨林斯的论述亦有类似的评价。
(10)尽管萨林斯基本赞成斯特拉森的结论,但他与拉姆齐(Alan Rumsey)私人交流时,他们一致认为斯特拉森的看法存在无法解释的困境,即美拉尼西亚人既是个体又是非个体。萨林斯认为,斯特拉森的意思很可能是:非个体的人(a dividual person)是单独的实体(an individual entity)。
(11)比如,若未能将“渗入到彼此实存”中却因战乱离散的恋人所经历的“破碎与残缺”与亲属之间的存在相互性进行区分,那么,作为亲属关系之独特性质的存在的相互性就不可能成立。
(12)在王斯福看来,萨林斯所说的存在的相互性亦在友谊和个人间的信任中出现。这便是说,存在的相互性本身并非亲属关系的特点,而亲属关系区别于其他关系之处并未被萨林斯说明。
(13)罗伯特·金对萨林斯文风的批评就更为严厉了。他说,萨林斯要求读者趟过一个58个单词的句子,其中又会遇到四个未被解释的术语和一次三重否定。他不得不反复阅读多次以发现萨林斯究竟在说什么。根据文本可读性评价标准来看,萨林斯以那个句子所表明的对读者的态度与朱迪斯舞娘俱乐部里最肆意的冒犯有得一拼。这语句又是陈腐的,若群体成员将生物血缘联系与其他种类的联系相结合,那么不论是人类,连蜜蜂和大象也是如此。这本书充满了这样的表述,它以复杂的语言掩盖了陈词滥调。
参考文献:
[1] Marshall Sahlins. What Kinship Is and Is Not [M].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3.
[2] Andrew Shryock. “It’s this, not that: How Marshall Sahlins solves kinship” [J]. 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2013:3(2):271-279.
[3] 蔡华. 人思之人: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统一性[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
[4] Robert King. “Just Growed Stories: A review of What Kinship Is-And is Not” [J].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11(2013)3:155-157.
[5] Robert Parkin. “Review: Marshall Sahlins, What Kinship Is-And Is Not” [J].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2013:Vol.86,No.1:293-301.
[6] David Schneider. A Critique of the Study of Kinship [M].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4.
[7] 蔡华. 汉族父系制度与中国亲属法的缺失[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8(5)
[8] 张帆. 血浓于水:华北高村汉族的亲属制度[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
[9] Stephan Feuchtwang. “What is Kinship?”, “Comment on Sahlins, Marshall. 2013. What kinship is –and is not”[J], 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2013:3(2):281-284.
[10] Cai Hua. l’homme pense par l’homme[M], Paris: PUF,2008.
[11] 蔡华. 纳人亲属制度的结构与婚姻/家庭悖论的终结. 公共理性与现代学术[C]. 北京:哈佛燕京学社和三联书店,2000.
整合讯息
共享学术

中国民族学学会
长按二维码关注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4520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45205号